作者:贾鹤鹏
编辑:Yuki
前段时间,在我的 《中国的科学传播,真的达到效果了吗?》 发表后,很多读者留下了宝贵评价。其中最集中的一类问题是, 说得没错,但是该怎么做?
此处有必要结合大家的问题,谈谈重视传播效果,对中国的科学传播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要澄清中国语境下有关科学传播的诸多问题。
从提供知识到预期效果
在 《中国的科学传播,真的达到效果了吗?》 一文的留言中,几位读者都提到科学知识的问题。有的说普及科学精神更重要,有的则质疑,科普不普及知识,能普及什么呢?
科学普及当然要传授知识 。但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我们需要认识到, 知识并不总是带来预期的态度 ;接受知识要受到受众各种特定情况和认知习惯的影响;知识可能与极化态度形成复杂的互动;最后,更重要的是,吸纳知识本身(不论是否接受)可能就意味着特定的态度。
以气候变化的传播为例。欧美社会主流科学界和科学传播界,对传播气候变化的主流知识可谓不遗余力。但在美国,始终有30%左右的公众不相信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这一主流科学结论。这些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有人在。·

(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制作的环保主题纪录片,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难以忽视的真相》)
影响人们是否认同气候变化科学的因素,有很多在知识范畴之外。简单的如极冷或极热的天气(反常极冷天气,就会导致人们不相信认为全球变暖的气候变化科学),或者人们之间的交流(自己圈子里的人是否认同气候变化),或者党派属性(大多数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不认同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复杂一点的则包括人们是否注意到科学家中有不同意见,或者是否觉得介绍气候变化的人看起来像科学家。
还有更加复杂的。对于一小段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知识表述,如果使用“气候变化”一词,则原句在自由派与保守派眼中的可靠程度没有区别。如果使用“全球变暖”(在日常语境中等同于气候变化)一词,相比民主党,共和党人会认为这段话看起来更像可靠的知识。原因在于,共和党或保守派人士不愿意承认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事实,所以更倾向于使用“全球变暖”一词,这样一旦出现反常变冷天气,他们就可以振振有词地驳斥全球变暖的结论了。
不仅如此,人们判断一个陈述是否属于知识,这本身都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比如,看到电视上一个学者模样的人在讲气候变化时,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就比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更觉得讲座者像一个科学家。这也就意味着, 美国人都觉得科学家靠谱,科学家讲出来的知识靠谱,但他们在谁是科学家,什么算是知识这一点上却有很大的分歧 。

(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TED上演讲|《难以忽视的真相》)
所以,强调传播效果的重要性绝不是停止传授知识,而是必须认识到,知识的效果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在 《中国的科学传播,真的达到效果了吗?》 一文中还提到了其他限制性因素,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人们的注意力有限,会本能忽视与己无关的信息。其他的包括负面信息偏见,先入为主偏见等等,也都会影响人们如何认定知识,如何采纳何种知识。
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需要普及知识,但不是讲过就完了。而是要在 一开始就考虑讲给什么人听,如何吸引他们的关注,如何克服他们的成见 (成见可远不止是气候变化或转基因这样的争议话题。一个养生,就有多少成见需要克服呀),如何继续学习,如何把知识转换为态度。
读者评论中也提到科普应该更重视普及科学精神。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有关啥是普及科学精神,我觉得总体上学界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说的普及科学精神,大概应该指培养公众应用理性和逻辑思维,并遵循科学程序来做出各种决策。但如果从传播效果的角度分析此事,人类的认知规律及其各种偏见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比如全民公民科学素养测试题中有一道是否认同双盲临床试验效果的题大概可以体现科学精神。但要受众认可双盲试验的效果超过江湖医生的“妙手回春”,就要他们对科学的解释方式给予更多关注,而不仅仅是依靠逻辑。
我们的科普真的不讲效果吗?
在 《中国的科学传播,真的达到效果了吗?》 一文中,我多次提到,中国科普或科学传播主要关注科普产品供给,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做的工作,完全没有效果。从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开始推动科普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强调,要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要寓教于乐,要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普及科学。
本世纪转基因争端肇起,生物科学家们和一些科普研究者又很快断言,政府和科学家公信力缺失,导致公众不相信有关转基因的主流科学结论。

(本世纪转基因争端肇起|Pixabay)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各种科普新媒体风起云涌,各种幽默话语、动图、调侃跃然纸(屏)上。与此同时, 用流量衡量科普效果一时成为业内时尚 。
所有这一切,不都是为了有更多人能获得被普及的科学知识么?即便用我们在 《中国的科学传播,真的达到效果了吗?》 和本文上面介绍过的一些理论视野,这些做法也都有根有据。比如喜闻乐见是为了提升受众注意力,寓教于乐可以促进学习情绪,浅显易懂则可以规避公众对未知领域的敌意。认识到公信力缺失与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关系,正是把科学传播中经常考察的信任与态度联系在一起,网络时代的各种调侃用语,则与传播学者界定的社交媒体传播的去中心化有关。
既然如此,为啥还说我们不注意效果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看美国的情况。我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效果研究是美国科学传播研究的核心。 但在现实中,影响人们认知、态度乃至行为的,可能有上百个因素,学者充其量也只能调控其中一部分因素,而这些调控所产生的效果,有可能在科普实践中就被我们未知的因素冲销掉 。
我在 《中国的科学传播,真的达到效果了吗?》 中提到了美国健康传播注重效果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比如劝导公众戒烟戒酒,鼓励孩子们增加锻炼。在这些案例中,得到传播学者们支持的公共卫生人员,通过大量公益广告来影响公众行为,这些广告中具体强调的因素往往是经过学者事先研究的。比如我本人参与过一项鼓励高中生增加体育锻炼的研究,就事先鉴定出导致高中生体育锻炼不足的最主要因素,是他们对功课繁重的心理预期。这样在公益广告中突出能克服这种预期的各种因素,就会有更好的说服效果。

(高中生体育锻炼不足|Pixabay)
但其实也有不成功的例子。1990年起美国国会累计批准了10亿美元用于减少高中生的大麻使用。相信支持这一耗资巨大的项目的健康效果研究应该不在少数(大部分健康传播的理论在那之前已经成熟了)。但到1999年项目结束时,美国高中生中的大麻使用不降反升。所以效果研究也不是解决所有传播问题的万灵药。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还能说中国的科普不重视效果吗?或者,我们还有必要从效果评估的角度来衡量科学传播呢?
科学传播,怎样考量效果?
我的答案是,我们仍然有必要从效果评估的角度来衡量甚至指导科学传播。
一方面,虽然我们在很少进行效果研究的情况下,仍然能取得科普工作的效果,这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实践层面的一些工作习惯,并没有从理论上去把这些因素变量化,所以很多寓教于乐的行为很难成为精准的可以预计效果的科普措施。
但另一方面,对于提升中国科普工作质量而言,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思考维度,那就是要 从科普该向什么人负责的角度来思考 。实际上,虽然我们70年来一直强调喜闻乐见的科普,近年来又不断重视用网络流量来衡量科普产品受欢迎程度,但这些生动的科普形式更多成为了一种行动惯性,实际上并不是充分考虑和评估了受众科普需求的结果。
在这种行为惯性下,执行者在设计和执行一个科普项目时,更多是考虑生动的形式是否符合了领导的预期,或者是否符合同事或同行们的常规做法,而不是是否能做到针对具体人群的效果最大化。
把知识乃至生动形式的知识供给作为对上级负责而不是着眼于对受众的影响,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以至于我们很难关注。就在写完这篇文章初稿后,我从父母家下楼,发现楼道里贴着一幅禁毒广告招贴画。

广告的标题是“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下面写着各种反毒品的知识。禁毒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它又不是普通人每日要关注的事项,与老百姓并没有切身利益关系。既然这样,这样的广告如何从让百姓愿意关注和了解广告中的戒毒、防毒知识呢?写完这段话,我在谷歌里随手用图片检索方式搜了一下”anti-drug ads”,出来的都是下面这类广告画面。

哪个广告对个体认知更有效果,恐怕不言而喻。在后面的“科学传播的科普”系列专栏文章中,我会应用视觉传播的理论再和大家探讨下科学传播的效果在这类公益广告中的作用。
当然,有人会说,禁毒这件事情,其实不看老百姓到底学了多少禁毒知识,而关键看公安抓得严不严,以及公众对禁毒措施是否被严格执行的预期。所以上面的禁毒广告能体现国家机器强大的威慑力就够了。
我们可以同意这个观点(实际上这涉及到 《中国的科学传播,真的达到效果了吗?》 所探讨的中美两种社会和政治传统对待公共治理的不同态度和采纳的不同路径),但回到科普供给的角度,对效果的传播就更显得重要了。因为在科普场景下,没有公安人员会拿着枪强迫你学习科学知识,提升科学态度。
科学传播走向何方?
在互联网时代的科普场景下,着眼于提升科普对个体受众的影响,比停留于提供喜闻乐见的形式以获得上级认可更加重要。比如,在网络上传播科普信息时,很显然大部分科普内容不适用于每个受众,所以单纯以互联网点击量来评估效果是不合适的。但如果点击量成为了正式的或默契的考核标准,那点击量到底与用户接受有什么关系,往往就不在科普工作者考虑之中了。
所以,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考虑科学传播,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一些指标,增添一些生动形式的问题。 它代表着一种对科普目标的根本转向,变成以受众为核心来思考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谈到该采取什么具体的手段来做效果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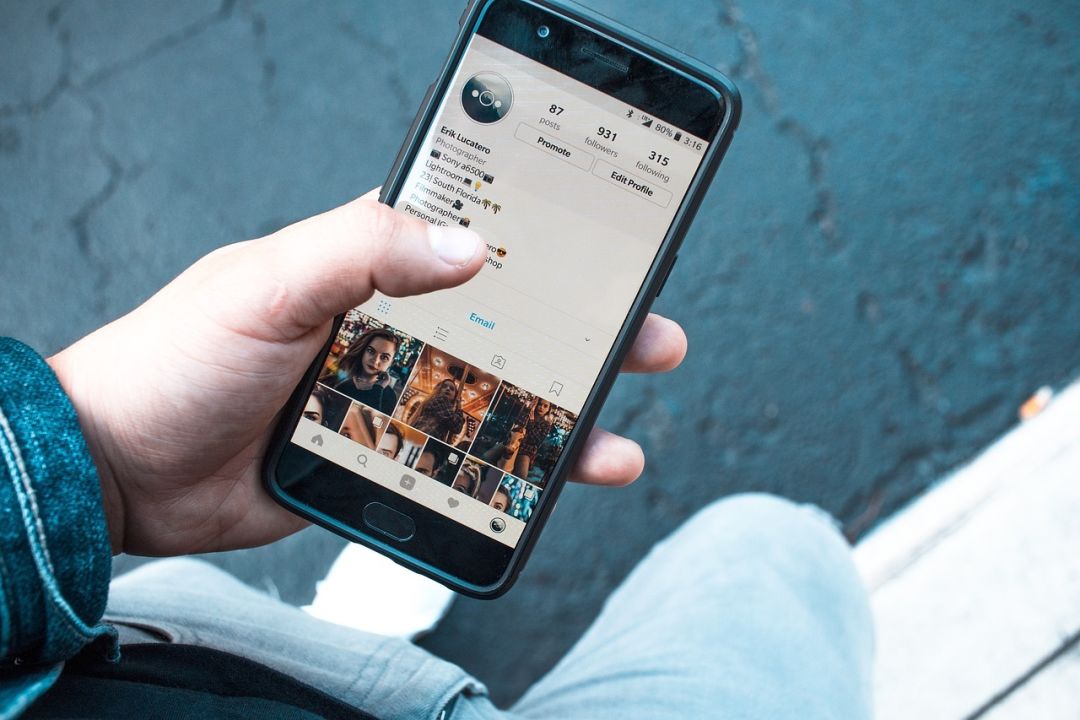
(以受众为核心思考问题|Pixabay)
刚才提到,即便完全基于传播效果,影响人们态度的因素也很多,我们甄别出来并能加以实际利用的,最多不过数十个,那怎么能确保我们设计的科普工作真有效果呢?这里需要指出,有关传播效果的学术研究与科普实务是不同的。学术研究更加关注的,是我们如何从拓展知识的角度,把握特定的因素产生何种效果。这些研究直接应用到科普实践,可能效果有限。
但这些学术研究日积月累,就可以以综述或评估报告的形式产生对实践的指导,或者至少是启示。比如美国科学院每年都会就科学传播出版的数本报告(全部可以免费下载),基于各种文献阶段性地评估在特定方面(比如公众的风险感知及其调控因素),我们的认识取得了什么进步,还有哪些认识上的盲区,现有的知识能在什么方面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做出科学决策。

(美国科学院网站|nasonline.org)
在科普效果评估的具体形式上,这种目标转向也代表着一个重大的变革。我们现在当然有很多评估工作。引导我走上科普道路的专家之一,中国科普研究所的郑念研究员就是开拓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之一。但如果我们做科普的目的是着眼于提升个体公民的素养、科学态度和他们的科学行为(以及如读者评论中所说,他们的科学精神),那么我们评估的重点就要从衡量各种科普供给的标准——活动数量、参加人数、政府投入、到场专家乃至领导批示等等——变成受众知识获取程度、态度改变和行为动机等指标。
同样,如果我们确定了以公众受影响程度作为科普的主要目标,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系统地引进和考量各种基于传播效果的理论和做法,根据中国环境做出针对性的研究,并进而从中国需求出发进行理论和实务创新。如我在 《中国的科学传播,真的达到效果了吗?》 一文中所说, 我们现在不缺做这方面研究和实务的能力,而是缺少鼓励这些研究和做法的氛围和评估体系 。
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如果我们做科学传播研究的目的是提升公众的素养,改变他们的态度,改进他们的行为,那我们绝对值得走上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作者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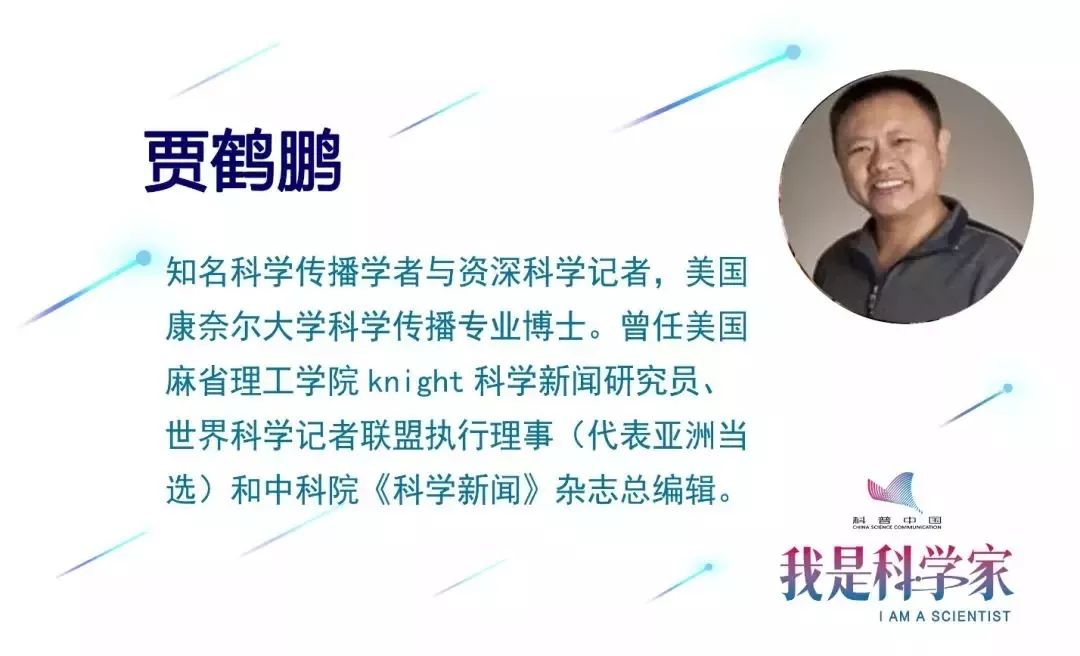
排版:凝音
题图来源:Pixabay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帮助
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