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那些动物好好地活在外面,我们不想因为我的研究让它们失去生命。”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我没有想到对于生命的担忧会发生在这一刻,而对于研究意义的迷惘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当时我尝试去解释,但是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学生有没有改变想法。很多人可能觉得保护研究就是去保护所有的生命。但其实我们不是兽医,也不是救助站。但这意味着经过这些之后,我们会变得麻木吗?其实也不是。

以下为李彬彬演讲实录
那一刻我受到了触动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次的活动,我叫李彬彬。
正如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我是一名自然保护研究者。当我跟很多人提到我的研究方向是自然保护的时候,很多人会突然一愣,然后尴尬又不失礼貌地微笑,但其实脸上就写着两个字:什么?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对我的工作有误解,他们要么觉得我整天是游山玩水,句号——没有任何其它事情了;要么觉得我身处在水深火热当中——需要风餐露宿,很辛苦;还有的人觉得我可能像圣母,只要遇到死了的伤了的小动物都要发给我看。大部分的时候我可能也就一笑了之。直到今年夏天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学生的微信,内容很多,但其实主要的信息就是:老师我不想打死老鼠。
当时我在印度带着另外一个团队,而她在中国负责跟印度研究相平行的研究,我们是想看放牧,也就是散养家畜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而生物多样性其中一部分工作是关注小型兽类,也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老鼠。当时我很着急,因为项目马上要开始了,于是我一个电话打过去。电话对面先是一阵沉默,接着我听到了浅浅的哭泣的声音,我心里一揪,就赶紧问到底怎么回事。学生说:“老师,那些动物好好地活在外面,我们不想因为我的研究让它们失去生命。”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我没有想到对于生命的担忧会发生在这一刻,而对于研究意义的迷惘就发生在离我这么近的身边。当时我尝试去解释,但是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学生有没有改变她的想法。这是很多人可能都有的一种固有思维,无关对错,他们可能觉得保护研究就是去保护所有的生命。但其实我们不是兽医,也不是救助站。 保护研究的目的也不是拯救每一个生命,它针对的是生命的一个集合 ,而这个集合可能是一个物种,可能是一个生态系统,也可能是更大的、所谓的生物多样性。而当这成为我们的研究目标的时候,我们去关注的是更大的一个问题: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评估动物门现在生活得好不好,它们有没有面临新的威胁,需要怎样的措施可以更长久地维持它们的繁衍生息。
所以当时我向她解释,其实小型兽类是我们了解得很少的一类群体,相对于大型哺乳动物,大象、狮子,或是鸟类,小型兽类的很多种类都不为科学界所知。然而要了解它们到底是哪一种,就需要用残酷的方式去取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它们的头骨是什么样子,它们的牙齿是什么样子。这也就意味着说,我们需要杀死个体。但倘若没办法准确地确定这个物种是什么,就无从评估它的数量、它的分布、它的状态,更无从去提及怎样提出更好的保护建议。

我们可以选择去在意每一条生命,但是有可能我们会错失去拯救一个物种命运的机会。所有的保护建议,所有的拯救措施,都是要基于数据之上的。没有这些研究和数据,当我们再去跟其他的利益或者决策相博弈的时候,可能就只剩下情怀二字。这二字听起来看似强大,但其实却是弱不禁风。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克服内心的恐惧 ,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很残忍,但是下一步我们想的却是怎样带着敬畏的心情去研究它们——怎么样去科学地设计取样的方式,更好的用最少的数量证明一个问题,怎么样减少动物的痛楚,或者它们死亡的痛苦。
但这意味着经过这些研究之后,我们会去适应,或者渐渐不再去感到难过吗?其实也不是。
我依然记得当初因为我的失误而死去的那只鸟。

这个故事要回到美国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可能知道佛罗里达,还有迈阿密,在它的最南端有一个地方很多人可能去过或者听说过,这个地方叫做KeyWest(基韦斯特,美国佛罗里达群岛最南的一个岛屿和城市),在KeyWest的东北100千米的地方有一片海岛,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公园,叫做干龟国家公园。
很多人乘船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看这里的碉堡,看它的文化意义。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其实在这个碉堡的后面,是一些重要的海鸟的繁殖场所,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研究的一个物种,它叫做乌燕鸥。这个物种每年大概二、三月份的时候就会来到这里繁殖,我们也会来到这个地方年复一年地调查它们的数量:我们捕捉正在繁殖的乌燕鸥,给它们带上脚环(环志),放走,第二年再捕捉和统计数量,从而了解整个种群数量和繁殖成功率。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的是鸟网,因为鸟网很细,很多鸟飞过的时候看不到这张网,就会被缠在网里,当你把鸟解下来的时候它是活的,给它戴上环,它就可以飞走。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是海风太大,所以这些鸟撞到网里之后会缠好几圈,根本解不下来,不管是对于鸟还是对于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

(乌燕鸥正在育雏。)
后来我们用回到最原始的方法。不像其它一些鸟类会做很漂亮的窝或是很精致的巢,这种鸟活得很粗糙,在土地上随便刨两下,它就觉得这是一个窝,会坐下来产蛋孵蛋。利用这个特性,我们可以走到它跟前,抓起不愿意放弃自己宝宝的燕鸥,快速带上环志,称重测量,赶紧把它们放回去。但这就要我们在它繁殖最重要的时间进入到它的繁殖地,而且还在不经意间踩碎了一些蛋,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立马终止了这种调查方式,开始了另一种。

图片上是我,我拿的就是后来用来捕鸟的工具。它其实是一个捞鱼的渔网,刚拿到渔网的时候我还疑惑说怎么可能拿这个来捕鸟,鸟在天上飞,鱼在水里游,我拿着渔网去捞鸟?经过一两天痛苦地挣扎之后,我发现其实是有办法的。这些鸟会从繁殖地起飞,悬浮在低空当中,等风一来它们会乘着风出海捉鱼。所以在风来的这一瞬间,是有机会从后面它看不到的地方一网把它捞住的。经过一些训练之后,我们每个人每天基本上可以捞到三四十只鸟。起早贪黑去捞鸟不是问题,手臂酸疼也不是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海风很大,鸟飞得很快,所以网的速度必须是要有的。这么长长的一个网,在海风的这种吹袭过程中,是要花费更大的力量的,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悲剧。
当时我捞一只鸟的时候,手里突然一颤——我没有捞住它,而是打到了它,接着我就看这只鸟落到了地上。我跑过去捡起这只鸟,发现它翅膀已经折断了。而就在几分钟之后,我另外一个同事也由于相同的原因打断了一只鸟的脖子。因为这个地方离主岛很远,把它们送到救助的地方很困难,所以当时决定进行人道处死。不管是我们两个当事人,还是我们的同事,还是已经工作了50多年的老教授,所有人的心是崩溃的。我们停止了所有的调查工作。我本以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查,我可以坦然面对这样的意外,但这时我发现不是的, 我发现那种自我责难,就像暗自生长的霉菌一样,根本无法抵挡 。海风吹在脸上,泪就不自然地流了下来。我给它喂了最后一口水,把它放到了小箱子里面送到了老师的船舱。“它很好,”他说,“没关系,后面的事情交给我,你去吧。”
每次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内心还是会有波动。但是当你问我后不后悔参与这个调查,后不后悔去抓这只鸟,我依旧会说,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倘若没有这年复一年近80年的调查,我们不知道它们会飞向非洲去觅食,回到这里来产卵;我们不知道一些鸟有着74岁的高龄,还依旧重复着这条道路回到这里来繁衍生息;我们更不知道让这些鸟死亡的最大原因不是别的,其实是海上的飓风,而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这些飓风的频率一次次地增加,它们的未来会面临更加危险的处境。
如果不是基于数据、研究,这些结果永远不可能以这么清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想办法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可以利用现在的科技,比如说给一些鸟佩戴上卫星定位系统,这样我们只用捕捉很少的鸟,就可以更详细地获得它迁徙的路径和情况;我们不再去捕捉个体,就可以直接通过粪便里、毛发中的DNA鉴别;或是我们研究出通过足迹就可以识别熊猫、大象、北极熊的个体甚至到它们的性别和它们的亲人关系的方法。
这些方法在一步步帮我们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怎么样用有限的数据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答我们应该去保护谁。这是一个先后问题,我们不可能保护所有的物种,我们重视的是那些已经濒危的或者是一个地方特有而其它地方不可能再出现的物种。这也就意味着在个体生命和物种的命运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倾向其中一个。
保护要回到“人”身上

(左一、左二:别人眼中我的工作。右一:我实际的工作。)
我的另外一个研究重点是大熊,有的时候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状态。很多人一听说我研究熊猫,脑中会想到这样的场景:穿上可爱的熊猫服跟它们近距离接触。但是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这可能只是我10年工作中不到10天的经历。而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在野外行走,接触它们的痕迹,比如说它们的粪便,它们的食迹,它们睡的巢穴,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去推断,到底熊猫的栖息地是如何根据环境而变化的,它们云游的范围有没有因为人类活动而减少,从而去确定哪些地方应该建立保护区,哪些地方应该更好地管理。
保护不光是跟动物相关,跟自然相关,很大一部分是要回到人的身上。 保护科学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不仅仅是生态学,很大的一部分是政策、经济以及法律和社会学。

倘若一个物种因为自然过程弱肉强食,走向灭绝,我们不会去干预,因为这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灭绝。但现在的灭绝事件很大一部分是由人来产生的,或是由人而推动的。现在的灭绝速率是多少?是我们正常背景灭绝速率的1000倍。
起因是人,解决的方案也要回到人的身上。 就比如熊猫,很多人会觉得熊猫是已经走向灭绝的物种,但其实它不是,它其实是进化上的强者,它发展出了很多很强大的武器:咀嚼肌非常强大,可以一口把这个竹子咬成一个齐的断面;它特化出来了第六指,不是真正的拇指,而是腕骨的一部分,但是可以帮助它对握,这是很少动物有的能力,帮它更好地去握竹子来吃东西;它在野外也繁殖得很好,完全不需要人去教它怎样交配。但为什么我们现在关注这个物种?原因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影响导致它们栖息地减少。我们砍伐森林,发展农业,发展基础建设,铺开了道路的网络,这些都导致它们栖息地破碎化。所以我们需要去研究怎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而我们的研究又发现新出现了一种威胁,放牧。在一些地方我们的研究发现,经过10年大强度放牧的影响,竹林被咬成了光杆司令,有一些地方根本没有竹笋发出来,熊猫的食物受到影响,熊猫为了规避放牧非常严重的地区,被驱赶到更高更陡的山坡上。

(经过十年放牧影响的竹林。)
发现问题不是重点,重点是去想原因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的工作涉及到大量的入户访谈,跟一些利益相关方的讨论,和法律研究。我们发现整个问题很复杂。比如我们国家为了保护森林,颁布了很多很好的政策,退耕还林、天然林禁伐, 但在保护森林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当地居民的生计应该怎么解决? 是有一些很好的项目来帮助居民解决生计的问题,但是由于水电搬迁,他们可能不再居住在这个地方,或是地震影响了游客的来量,慢慢地又会演化出一种需求。我想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弥补当地经济收入的缺失。
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市场对于牛肉的需求的增加,对于这些肉产品的增加。可能大家觉得熊猫离我们很远,我们怎么会影响到它们? 但其实往往就是这些物质需求的增加,导致它们栖息地一步步被蚕食 ,比如我们对于木材的需求,对于金属的需求,对于食材的需求,以及对于牛肉的需求。
去伤心绝望还太早
我们在研究这些动物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发现就算我们尽再大的力,它们还是一个个的从眼前消失,在我们的奋战之下,还是有一片片的栖息地被蚕食。这时候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绝望,去伤心,我们真的走到了尽头了吗?
我记得我在美国读博的时候,我的导师站在台上,有人在台下问他,现在 我们面临一场场的败仗,为什么你还觉得地球有希望?我的导师说,因为我的学生 ,他指向台下的我们,一个个把我们的名字点了出来。当时我内心是感动,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直到我成为一名老师,发现有这么多的学生和年轻人愿意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的时候,那是一种触及内心的力量。但我也深知在这条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困难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因为对于人的误解。

这个暑假我接到了我的野外向导的一个电话,当时是美国的中午,中国夜里12点。我当时很着急,因为12点打来的电话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他在电话里说,你的学生喝醉了,在我这哭。我当时很懵,跟我想象的问题不太一样,我先责难了他一番,问是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他说跟我没有关系。几通电话之后我了解到,这是一个三个女生组成的团队,她们在野外工作,当地人很支持很配合,但是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你们是从城里来的,是娇气的女孩子,是官二代、富二代。面对这些称号,这些学生心里是不好受的。她们咬着牙,哪怕脚崴了,也要继续上山,因为她们不想带上这样一个名号。
这些压力和阻碍往往是来自于一种偏见。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写给想要做自然保护女生的一封信》。当时我收到了很多的来信,很多女生,也有一些男生说他们在选择不同专业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和瓶颈。我本来不想再去提这个事情,但后来发现我认为已经慢慢消失的偏见还是一次次地打在这些年轻人身上,这时候去说这个问题不是执念,也不是矫情,而是希望给那些还在自我怀疑,还在和偏见做斗争的年轻人一个肯定。 决定成功的是你自己,而不是你的类别 。如果像大家所说的,经过这些淘汰,留下了所谓合适的人,那为什么保护上面我们还在经历一次次的滑铁卢,我们还在失守一座座的堡垒。真的存在所谓合适的人或者合适的方法吗?我想不是的,我想用保护生物学泰斗爱德华威尔逊(E.O. Wilson)的话来想这个问题,他说,“The education of women is the best way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拯救环境最好的方法是给予女性教育,给予她们力量,给予她们改变的空间,去调动世界上另外一半的人口。 在我们还没有穷尽人力和智力的时候,还太早说人类没有指望。在我们还没有去发掘和调动人性中最美和最有智慧的一方面的时候,还太早去伤心绝望。
我经常有这么一个疑问,到底保护研究值不值得去做?可能我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但至少我可以肯定的是需要有这么一群人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去收集每一个数据,去系统地用科学的方法回答数据后面的信息,用这些信息去评估我们之前的成与败,去指出下一步的可能性。需要有这么一批人不被感情左右、不被道德绑架,去分析我们的痛处在哪里,去缝合我们的伤口。
希望在我解释了这些或美好或冷酷的误解之后,你也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或者至少去关注这么一群人,他们是自然保护研究者。
谢谢大家。
往期演讲回顾:
5张玩家地图,1000多万个游戏角色,谁才是这个虚拟城市里的头号大BOSS?| 罗训
“妈,求你别再转发这种文章了”,中老年人为何成为网络谣言重灾区?| 张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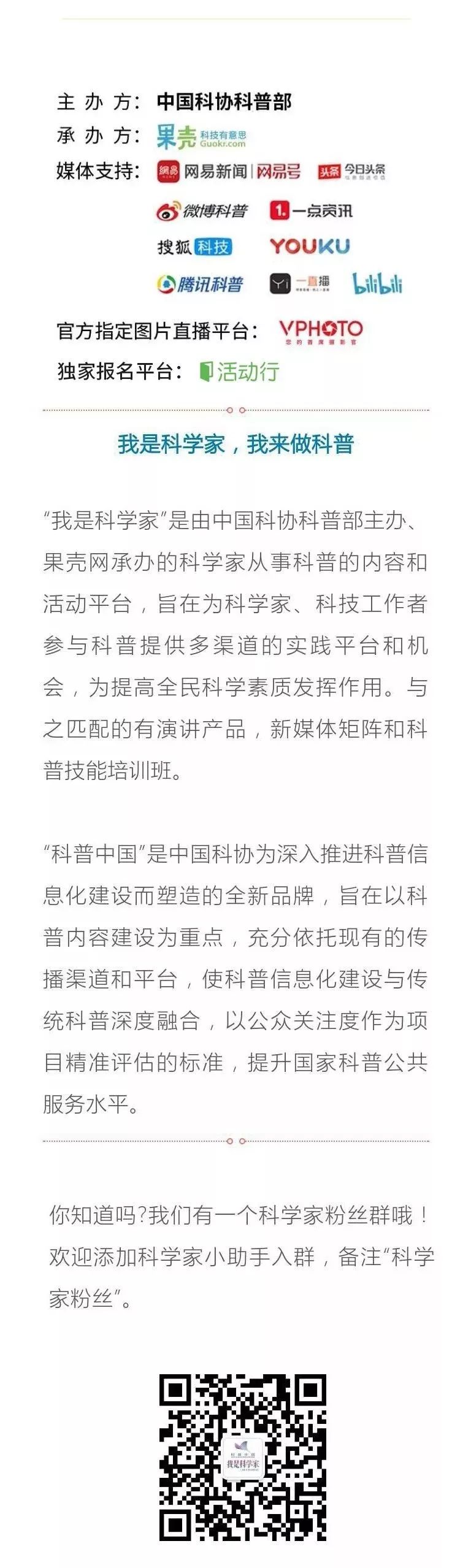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帮助
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