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双手布满老茧,脊梁被岁月压得微微弯曲,却一辈子没停下过忙碌的脚步。从我记事起,家的房前屋后总有鸡的身影 —— 从儿时连温饱都成问题的艰难岁月,到我十岁、二十岁,再到如今四十多岁,日子一天天变好,家里的生活早已不愁吃穿,可妈妈养鸡的习惯,却像扎了根的老树,怎么劝都改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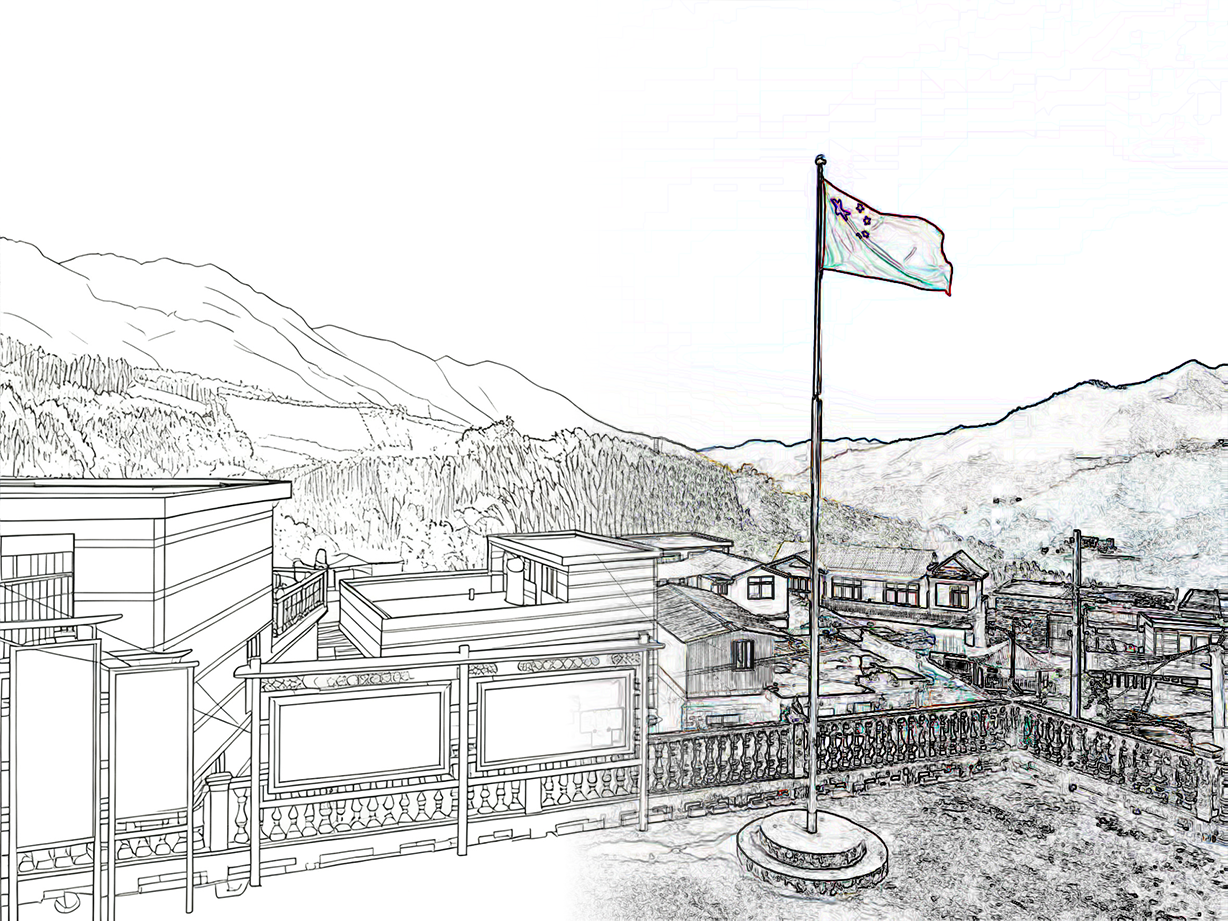
“妈,你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手脚又常麻木无力,高血压也得常吃药,别再养鸡折腾自己了。” 这样的话,我多年前就开始说,可每次都被妈妈轻描淡写地挡回来。她总攥着那把用了十几年的鸡勺,蹲在鸡窝边,看着十几只土鸡啄食,眼里满是温柔:“你懂啥?过日子哪能不养鸡?养着鸡心里才踏实。”
后来我才发现,妈妈养的哪里是鸡?简直是把鸡当成了宠物,当成了没在身边的孩子。她对鸡的照顾,细致到了骨子里。家里白天煮米粥、晚上焖米饭,妈妈做饭时总要多焖半锅饭、多熬三碗粥,哪怕当天的剩饭够喂鸡,也总怕 “鸡没吃饱”。吃剩的饭菜更是舍不得倒,连带着油汪汪的菜汤,都要小心翼翼倒进那个印着碎花的旧桶里,盖紧盖子存着。“汤里有盐巴,鸡爱吃,倒了多可惜。” 她一边擦着桶沿的汤汁,一边念叨,仿佛那不是剩菜汤,是什么宝贝。
到了冬天,菜地成了妈妈的 “鸡食补给站”。她挎着竹篮去摘白菜,一摘就是一大把,嫩的留着晚上炒着吃,剩下的老叶、菜帮,全都切碎了炖熟和剩饭喂鸡。看着,妈妈坐在小板凳上一点点把菜切碎,再倒进大铁锅里,添上柴火煮成稠稠的鸡食。看着她的额角渗出的汗珠,偶尔抬手揉一揉发麻的手腕 —— 那是常年劳累落下的毛病,可她从没说过一句累。
最让我揪心的,是鸡窝的卫生。夏天一到,鸡粪的臭味飘得满院子都是,苍蝇嗡嗡地围着鸡窝转,连带着家里也多了不少蚊子。我劝妈妈不养了,也省地打理,她却只是笑着摆手:“没事,扫扫就好了,农村哪有不养鸡的。” 可我知道,她的身体早就透支了。高血压让她时常头晕,手脚麻木无力得连端碗都要慢半拍。这些慢性病,哪一个不是常年起早贪黑、操心劳累熬出来的?
我渐渐明白,妈妈养的不是鸡,是她放不下的旧日子。以前村里没超市,买东西要走几里地,鸡下的蛋是家里的 “硬通货”;现在村里超市天天开门,可她总觉得 “不如自己养的放心”。尤其是我迟迟没结婚,家里少了些热闹,鸡的叫声成了她的精神寄托 —— 仿佛只要鸡还在,那些熟悉的日子就没走远。
少即是多,少了一些操劳,多一些幸福。我们从来不是说要放弃什么,而是当生活环境变了,学会调整习惯,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折腾。日子往前走,习惯也该跟着往前走,这样才能在新的日子里,收获更多的轻松与美好。
来源: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科学技术协会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帮助
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