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宙的时间长河里,地球的诞生是一段跨越数十亿到上百亿年的壮丽史诗。关于这颗蓝色星球如何从混沌中成形,科学界存在多种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传统的万有引力学说与新兴的正交碰撞膨胀力学说。它们如同两盏探照灯,照亮了地球形成与演化的不同侧面,却又在某些关键节点上指向相似的结论。让我们以对话的视角,揭开地球天文演化阶段的神秘面纱。
一、引力的 “聚集史诗”:从星云到行星的自然演进
万有引力,这个支配宇宙天体运动的基本力,为地球形成提供了一套被广泛认可的经典叙事。在它的框架里,地球的诞生是物质在引力作用下 “从散到聚” 的必然结果,整个过程始于 46 亿年前一片来源成谜的分子云。
太阳系的起点:分子云的收缩与原行星盘的诞生
彼时,早已形成的银河系边缘漂浮着一片巨大的分子云 —— 这是由氢、氦气体和尘埃颗粒组成的太阳系 “宇宙摇篮”。在自身引力的持续拉扯下,这片分子云团开始缓慢收缩。引力的独特之处在于 “正反馈”:物质越集中,引力越强;引力越强,越容易吸引更多物质。随着收缩的推进,云团中心的密度和温度急剧升高,当中心温度达到 1000 万摄氏度时,氢原子核发生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 —— 原始太阳就此诞生。
而太阳周围未被吞噬的物质,在旋转中逐渐扁平化为盘状结构,这就是 “原行星盘”。这个厚度约数十万公里、直径达数亿公里的物质圆盘,是太阳系行星的 “育儿室”。盘中漂浮着无数微米级的尘埃颗粒,它们如同宇宙中的 “积木”,在引力的微妙作用下,开启了地球形成的第一步。
地球胚胎的成长:从尘埃到原行星的漫长之路
在原行星盘中,尘埃颗粒的最初碰撞是随机的,但引力让偶然的相遇变成了必然的结合。静电吸附先让微米级颗粒粘合成毫米级团块;随着质量增加,引力开始主导聚集过程,团块成长为厘米级的 “星子”;星子继续碰撞、合并,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最终形成直径可达数千公里的 “原行星”—— 这便是地球的胚胎,如同现在小行星带上的物质。
地球胚胎的成长绝非一帆风顺。早期太阳系如同一个狂暴的 “碰撞场”,原行星之间的撞击频繁发生。其中最关键的一次,发生在地球形成后不久: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被科学家命名为 “忒伊亚”)以倾斜角度与地球胚胎相撞。这场剧烈碰撞将两者的部分物质抛射到太空,而这些碎片在地球引力的束缚下重新聚集,最终形成了月球。这一 “大撞击说” 不仅解释了月球的起源,还揭示了地球自转轴倾斜(造就四季更替)、自转速度变化(早期地球一天仅 6 小时)的根源。
天文到地质的转折:引力塑造的圈层结构
当地球胚胎通过吸积周围物质达到如今的质量规模时,天文演化阶段逐渐落幕。此时,引力展现出另一种关键作用 ——“重力分异”:重元素(如铁、镍)在引力作用下向中心下沉,形成致密的地核;较轻的硅酸盐物质则上浮,形成地幔和地壳。就这样,地球从内到外形成了清晰的圈层结构,为后续的地质演化奠定了基础。
在引力的叙事里,天文演化阶段的核心是 “聚集”:从分子云到原行星盘,从尘埃颗粒到地球胚胎,每一步都是引力主导下物质不断浓缩的结果。这个过程温和而持续,如同一位耐心的工匠,用数十亿年的时间将松散的材料雕琢成有序的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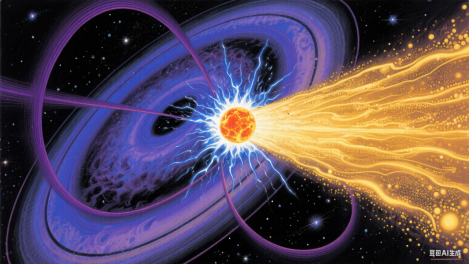
二、膨胀力的 “碰撞叙事”:从旧宇宙到新行星的能量转换
正交碰撞膨胀力学说为地球形成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视角。它跳出 “引力聚集” 的逻辑,以 “碰撞产生能量、能量驱动运动” 为核心,将地球的诞生与一场宇宙级的 “旧物终结与新物创生” 事件紧密相连。
宇宙的“重启”:正交碰撞与新粒子的诞生
新理论的起点,是当前宇宙形成前的一场剧烈碰撞。那时存在两个或多个 “旧物体”(前宇宙残留的高密度物体),它们的质量与能量的乘积被称为 “旧质能”。当这些旧物体以 “正交碰撞”(运动方向相互垂直)的方式相遇时,一场颠覆性的质能转换事件发生了[1]:旧物体的质量大量转化为能量,催生了无数 “新粒子”—— 也就是 “新物态”,即 138 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
该理论强调,新旧世界之间存在 “信息隔离”:旧物体的物理规则与新粒子完全不同,就像两个独立的宇宙系统,彼此无法传递信息。碰撞后,新粒子携带巨大能量,开始向各自的 “目的地” 加速运动。这种运动被称为 “膨胀力下的加速运动”,它包含两个分量:径向的直线加速(远离大爆炸时的碰撞点)与切向的圆周运动(绕目的地旋转),最终呈现为螺旋状轨迹 —— 这与我们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如行星绕日、水流漩涡)高度契合。
太阳系的 “粒子奔赴”:从太阳到地球的成形
在这场碰撞诞生的新粒子中,有三股关键力量分别指向太阳、地球和月球的中心。前往太阳的粒子数量最多、加速度最大,它们如同奔赴熔炉的燃料,在太阳中心发生多角度和正交碰撞。碰撞产生的动量转化为热量,使中心温度飙升至数千万摄氏度,氢核在此发生聚变——这正是太阳持续发光发热的能量来源。即便到今天,太阳上的粒子仍在发生碰撞,维持着核聚变反应,并向宇宙空间辐射包括光子在内的各种粒子。
奔向地球中心的粒子则演绎了另一番历程。先期到达的粒子在中心聚集,形成温度较低的固态地核;后续到来的粒子与地核发生碰撞甚至正交碰撞,动量转化为热量,让地球外层物质逐渐熔融,形成液态和气态圈层。就这样,地球从内到外形成了固态、液态、气态的垂直分层 —— 与引力学说的 “重力分异” 结果相似,但驱动力截然不同:前者是引力导致的 “重沉轻浮”,后者是碰撞能量导致的 “内层先固、外层后融”。
粒子的运动还塑造了地球的自转。大量粒子以 “吸积盘” 的形式绕地球中心旋转加速汇合,如同水流漩涡般集中角动量,让地球自转速度不断加快。最终,在天文演化阶段结束时,地球自转达到最快,两极位势高度高于赤道的形状也由此固定。
月球的形成过程与地球类似,只是那股宇宙大爆炸后趋向月球中心汇聚的粒子数量少于地球,更少于太阳。月球也经历了与地球相似的天文演化阶段,在该阶段结束时,其表层温度达到最高,自转速度最大,也形成了内部固态、中间液态和外部气态的分层结构。
天文与地质演变的分野:温度作为关键节点
膨胀力学说对地球演化阶段的划分十分清晰:当所有向地球中心汇聚的粒子都进入圈层结构,地球整体温度达到最高时,天文演化阶段宣告结束;此后,地球表面温度开始下降,进入以能量释放和圈层互动为主的地质演化阶段。
在这个框架里,天文演化阶段的核心是膨胀力使 “粒子聚集与能量累积”,地质演化阶段则是 “能量释放与结构调整”,两个阶段的界限由 “温度峰值” 明确界定。

三、两种叙事的碰撞与共鸣:科学探索的并行轨道
引力与膨胀力的解释,看似针锋相对,却在诸多方面呈现出奇妙的 “共识” 与 “分野”。
共识:演化阶段与圈层结构的必然
两种学说都认可,地球的演化分为 “天文阶段” 与 “地质阶段”。天文演化阶段是地球的 “成形期”,决定了它的基本质量、体积和圈层结构;地质演化阶段是地球的 “改造期”,塑造了地表形态、大气成分和生命演化的环境。
它们也都认同,地球最终形成了固态内核、中间液态层与外部气态层的分层结构,且自转与公转的特征(如赤道略鼓、两极稍扁的形状)是天文演化阶段的直接产物。这些共识,为我们理解地球演化提供了基本锚点。
分野:驱动力与过程的本质差异
在 “如何形成” 的核心问题上,两者的解释截然不同。传统万有引力学说的关键词是 “引力主导、渐进聚集”:从分子云收缩到原行星盘形成,从尘埃颗粒合并到地球胚胎成长,每一步都依赖引力的 “拉合” 作用。它强调过程的连续性,认为地球的形成是物质在引力作用下 “从小到大、从散到聚” 的渐变结果,且有陨石成分分析、原行星盘的天文观测等的证据支持。
正交碰撞膨胀力学说的关键词是 “碰撞驱动、能量转化”:它将地球的形成追溯至前宇宙中物质的正交碰撞,认为新粒子的定向加速运动与碰撞是地球成形的核心动力。该学说强调过程的爆发性与定向性,用 “粒子奔赴目的地” 解释物质加速聚集,用 “碰撞产热” 解释圈层熔融。银河系中大量星云正在向其中心加速旋转式汇聚和碰撞,这为理解宇宙起源提供了新的逻辑框架。
两者的天文演化时间尺度亦有不同:引力学说始于 46 亿年前一片来源成谜的分子云,留给地球天文演化的时间仅有数亿年;膨胀力学说则从 138 亿年前宇宙大爆炸时便开始计时,描述分股新粒子的汇聚过程,其给予地球演化的时间长达 90 余亿年,与银河系的演化时长相当。
对话:科学进步的交替
两种学说的碰撞,恰恰体现了科学探索的本质。对于传统引力理论,牛顿以统计数学形式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则用几何数学形式构建广义相对论,二者共同搭建了理解地球形成的基础框架;膨胀力学说跳出传统视角,尝试从更根本的质能转换角度解释宇宙演化,虽需更多验证,却拓展了人类认知的边界。
正如物理学家玻尔所言:“真理的反面或许是另一个真理。” 引力与膨胀力的叙事,未必是非此即彼,而是从不同维度、不同世界观逼近地球形成的真相。在物理学层面,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未绝对肯定引力的存在。若他们站在膨胀力的世界观上,或许会为太阳系形成提出另一种数学表达。苹果下落是双方公认的事实,分歧仅在于将其归因于引力还是膨胀力。而对引力的认知,还依赖于尚未发现的引力子。
又如当代物理学泰斗杨振宁所言:“如果你问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为整个这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 爱因斯坦也曾表示,造化者一定存在!未来,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我们或许能找到两种理论的交汇点或接力处,拼凑出更完整的宇宙、银河系、太阳系及地球诞生的图景,或书写出类似从 “地心说” 到 “日心说” 的动人历程。
结语:未完待续的地球故事
从分子云的引力收缩到旧宇宙物质的正交碰撞,从尘埃颗粒的缓慢聚集到新粒子的定向奔赴,地球的天文演化阶段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谜题。无论是引力的 “聚集史诗”,还是膨胀力的 “碰撞叙事”,都在诉说同一个奇迹:在宇宙的随机与必然之间,地球恰好成为了孕育生命的摇篮。
天文演化阶段的结束,并非故事的终点,而是地质演化阶段的开端。当地球表面温度从峰值开始下降,板块运动、大气环流、生命诞生的大幕缓缓拉开。关于这些后续篇章,我们将在下次对话中陆续探寻 —— 毕竟,地球的演化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宇宙力量与自身调整持续互动的结果。
或许,正是这种多元的解释视角,让太阳系和地球的诞生故事更加迷人。它提醒我们:科学的魅力不在于找到唯一答案,而在于永远保持好奇,在不同理论的碰撞中,一步步接近宇宙的真相。
参考文献
[1] Qian WH (2025) Expanding Force in Astronomy and Updraft Force in Meteorology. J Mod Phys 16: 267-285.
来源: 钱维宏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帮助
帮助
 钱维宏
钱维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