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斗蛐蛐,白露开盆。早虫立秋脱殻(音“俏”),至此已有一个月,可以小试其才了。在上局之前,总要经过“排”。所谓“排”,是从自己所有的蛐蛐中选份量相等的角斗,或和虫友的蛐蛐角斗。往往赢了一个还不算,再斗一个,乃至斗三个。因为只有排的狠,以后上局心中才有底,同时把一些不中用的淘汰掉。排蛐蛐不赌彩,但须用“称儿”(即戥“等”子),“腰”份量,相等的才斗,以免小个的吃亏。自己排也应该如此。当然有的长相特别好的舍不得排,晚虫不宜早斗得也不排,到时候直接拿到局上去,名叫“生端”。
称儿是一个长方形的匣子,两面插门。背面插门内镶有玻璃,便于两面看份量。象牙制成的戥子杆,正背面刻着分、厘、毫的标志,悬挂在匣子的顶板下。杆上挂着戥子铊。随着称儿有四个或六个“舀子”,供几位来斗者同时使用。少了不够分配,蛐蛐约不完,耽误对局进行。
舀子作圆筒形,用竹筐内壁(竹黄)或极薄银叶圈成,有底有盖,三根丝线将筒和盖连接起来。线上端系金属小环,可挂在戥子的钩上,这是为装入蛐蛐称份量而制的。几个舀子重量必须相等,毫厘不差。细微的出入用黄蜡来校正,捻珠黏在三根丝线聚头处,籍以取得一致。
白露前几日,组织斗局者下帖邀请虫友届时光临,邮寄或事人送往。帖子内容如下:
兹定于八月十一日下午二时会斗秋虫敬请
光临劲秋谨定
盆设朝阳门内南小街一七五号旁门
与一般请帖不同的是邀请者具名不写姓名,而写局上所报的“字”。姓名可以在请帖的封套上出现。
蛐蛐局也有不同的等级。前秋的局乃是初级,天气尚暖,可在院子内进行,有一张八仙桌,几张小桌和椅子、凳子就行了。这样的局我也举办过好几年,用我所报的字“劲秋”具名邀请。院子是向巷口已开张的赵家灰铺租的,每星期日斗一次。局虽简陋,规矩却不能错,要有五六个人就能唱好这台“戏”。
一个司称,需提前到局,以便将舀子的份量校正好。校正完毕,坐在称儿前,等待斗家将虫装入舀子送来称重量。

一个司帐,画好表格,记录这一局的战况。表格有个固定格式,已沿用多年,设计合理,简明周密,一目了然。(这里不列明细样张)
司帐者桌上摆着笔墨、纸张、裁纸刀等,兼管写条子。条子用白纸或色纸裁成,约两寸宽,半尺长,盖上司帐者印章,以防有人作弊,更换条子。斗家到局,先领舀子,装好蛐蛐,送去过秤。称好一虫,司称高唱某字重量多少。司帐在表格的第二格内写报字,第三格内用苏州码子写蛐蛐的份量。另外在一张条子上写报字和份量,交虫主持去,压在该虫的罐子下。各家的蛐蛐登记完毕,就知道今天来了那几家,各有多少条虫,各虫份量多少。斗家彼此看压在罐下的条子,就知道自己的蛐蛐和谁家的份量相等,可以栓对。司帐根据表格也会不时的提醒大家,谁和谁“有对”。
一人监局,站在八仙桌前,桌上铺红毡子,旁放毛笔一枝,墨盒一个。桌子中央设宽大而底又不甚光滑的瓦罐,名为“斗盆”。两家如同意对局,各把罐子捧到斗盆一侧。监局将两张条子并列摆在桌上。这时双方将罐盖打开,进行”比相”。因为即使份量相等,如一条头大项阔,一条头小项窄,项小的主人会感到吃亏而不斗。比相后同意对局,再议赌彩。早秋不过赌月饼一两斤。每斤月饼折钱多少,由司帐宣布,一般为五角或一元。议定后,监局将月饼斤数写在两家的条子中间,有如骑缝,字迹各有其半。
双方将蛐蛐放入斗盆,各自只许用黏有鼠须的芡子撩逗自己的蛐蛐,使之有敌来犯。当两虫牙钳相接,监局须立即报出“搭牙”,算是战斗已经打响,从此有胜有负,各无反悔。不论交锋的时间长短,回合多少,上风下风有无反复,最后以“一头一面”判输赢。所谓“一头”、“一面”乃是一回事,即下风蛐蛐遇见上风,贴着盆腔掉头逃走。如此两次,便是输了。倘向盆腔相反方向掉头逃走,名曰“外转”;向前逃窜,名曰“冲”,都不算“头”或“面”。不过监局也须大声报出,好让虫主和观众都知道。监局实负有裁判员的职责。胜负即分,监局在胜者的条子上写个“上”字,在负者的条子上写个“下”字。两张条子一并交到司帐那里。司帐根据条子在表格上胜者一栏的第一格里写蛐蛐的重量及所赢月饼的斤数,在负者一栏的第四格里写蛐蛐的重量及所输的月饼斤数。两张条子折好存在司帐处,趟有人要复查,此是凭证。各家结账时据第一、第四两格的输赢数字,结算盈亏。

上述三人是局上的主要人员,此外还须一两人沏茶灌水,照料一切。一局下来,他们分抽头二成所得,每人可得几块钱。
倒不是我夸口,三十年代由我邀请的初级小局,玩得比较高尚文雅。来者岁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但很少发生争执或有不局气的行为。赌彩既微,大家都不在乎。不少输了钱如数缴纳,赢了却分文不要,留给局上几位忙了一天的先生们一分了事。这当然和早秋季节有关,此时大小养家蛐蛐正多,心爱之虫尚未露面,骁勇之将或以亮相,但尚未立多少战功,所以上局带有练兵性质,谁也不想多下赌注。
中秋以后,天凉多风,院里已不宜设局。这时自有大养家出面邀请到家中对阵,蛐蛐局也就升了级。善战之虫已从几次交锋中杀了出来,渐有名声。赌彩倘仍是一两斤月饼,主人会感到和虫的身价太不相称了。
只要赌彩大了,事情也就多了,不同人物的品格性情也就一一表现出来。有的对上称约份量十分计较,老怕司称偏心他人,以致吃了亏。他在称的背面盯着戥子,嘴里唠叨着:“不行吧,拉了一点吧,您再往里挪挪。”所争的可能还不到一毛(即一毫)的重量。甚至有人作弊,把舀子上的蜡珠偷偷扣下一点。自己占了便宜却弄得舀子的份量不一致。被人发现,要求对所有的舀子都复查核对,把局吵了,弄得不欢而散。
斗前比相,更是争吵不休,总是各自贬低自己蛐蛐的长相,说什么:“我的头扁了,脖子细了,肚子大了,比您的差多了,不是对!不是对!”实则未必如此。有的人心中有一定之规,那就是,相上如占不到便宜,就是不斗。
在观众中,随彩的也多了。有的只是因为和虫主有交情,随彩为他助威。有的则因某虫战功赫赫,肯定能赢,故竞相在它身上压赌注。倘对局双方均是名将,各有人随彩,那热闹了。譬如“义”字和“山”字对阵,双方已议定赌彩,忽一边有人喊道:“‘义’字那边写‘爽秋两块’。”又有人喊:“天字两块。”对面有人应声说:“‘山’字那边写‘叨字两块’。”跟着有人喊:“作字随两块。”这时忙坏了监局,他必须在两边条子上把随彩人的报字和所随的钱数一一记上,分胜负后司帐好把随彩移到表格上。随彩者如没有蛐蛐,他的报字也可以上表格,只是第三格中不会有蛐蛐的分量而已。有时斗者的某一方不常上局,显得陌生,他就难免受窘,感到尴尬。因为观阵者都向对方下注,一下子就增加到几十元。如果斗,须把全部赌注包下来,未免输赢太大。不斗吧,又显得过于示弱,深感进退两难。

使芡子是一种高超的技艺。除非虫主是这方面的高手,总要请专家代为掌芡。运用这几根老鼠须子有很大的学问。但主要是当自己的蛐蛐占上风时,要用芡子激发神威,引导它直捣黄龙,使对方一败涂地。而处于下风时,要用芡子遮挡封护,严防受到冲击,好让它得到喘息,增强信心,恢复斗志,以期达到反败为胜的目的。但双方都不能做的过份,以致触犯定规,引起公愤。精彩的对局,不仅看斗虫,也看人斗。欣赏高手运芡之妙,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哪怪自古即被人重视,《蚟孙鉴》有专条记载运芡名家姓氏,传于后世。
清末民初,斗局准许用棒,在恩溥臣《斗蟋随笔》中有所反映,而为南方所无。对阵时,占上风上一方用装芡子的硬木棒轻轻敲打盆腔,犹如擂鼓,为虫助威。这对下风当然大大不利。三十年代已渐被淘汰,偶见使用,是经过双方同意的。
监局即是裁判,难免碍于人情或受贿赠而偏袒一方。这在将分胜负的时容易流露出来。他会对一方下风的“一头一面”脱口而出,甚至不是真正的掉头败走也被报成“头”、“面”。而对另一方下风时,“一头一面”竟支吾起来,迟迟不报。执法态度悬殊,其中必有不可告人处。
局上可以看到人品性格,众生相纷呈毕现。有人赢了,谦虚地说声:“侥幸。”有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向对方投以轻蔑的眼光。输了,有人心悦诚服,自认功夫不到家,一笑置之,若无其事。有人则垂头丧气,默默不语,一虫之败,何至懊丧如此?!更有面红耳赤,怒不可遏,找碴强调客观原因,不是说比相吃了亏,就是使火没使够。甚至埋怨对方,为什么催我上阵,以致没有过铃子,都是你不好,因此只能认半局,赌彩只输了一半。
上面讲到的局,一般有几十元的输赢,还不能算真正的蛐蛐赌局。真正的赌局斗一对下注成千上万,这只有天津、上海才有。据说在高台上斗,由一人掌芡,只许双方虫主在旁,他人无从得见。这样的局不要说去斗,我一次还没有参观过呢。即使有机会参观,我也不会去!
( 节选自《秋虫六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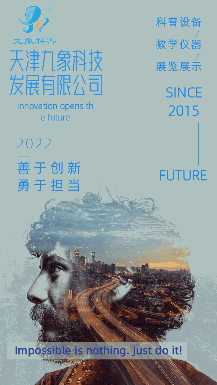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帮助
帮助
 CHN九象科技
CHN九象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