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整理/记者 吉菁菁 供图/张利
新媒体编辑/李云凤
【主讲嘉宾】

张 利(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长聘教授,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总规划师,首钢滑雪大跳台设计总负责人)

▲2022年2月21日《北京科技报》封面
▲本期首都科学讲堂视频回放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标志性场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和首钢滑雪大跳台“雪飞天”见证了奥运健儿们创造的每一个历史性瞬间。这两座场馆也以巧夺天工的设计,“绿色低碳可持续”建筑的典范,受到运动员和大众的欢迎和喜爱。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雪如意”是如何“打造”的?与工业旧址结合再利用的“雪飞天”为何选址首钢工业园?
❄ ❄ ❄
人因技术:突破“白象”问题的瓶颈
我是一个建筑师,也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总规划师和首钢滑雪大跳台设计总负责人。我从2014年下半年加入申奥团队,至今已为冬奥工作了七年多,是我个人职业生涯里一次很重要的学习体验。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意义,我个人理解是远远超过举办一次冬奥比赛的盛会,是我国借举办冬奥会的契机,通过冬奥建设实践和办赛以及赛后利用的实践,传达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把中国的理念和方法向世界传递的一个过程。
谈到冬奥场馆建筑,不得不提到一个现象。传说古代中亚国家的国王会将白色的大象赐予自己不喜欢的大臣,让他们因为饲养珍兽而倾家荡产。国际上也将因大型盛会兴建的场馆设施赛后利用不佳,被闲置或废弃的现象称为“白象”(White Elephant)。

华而不实的“白象”现象,曾是长期困扰奥运会的难题。尤其是冬奥会比赛涉及很多高难度项目,而难度越高的比赛,设施在赛后越难得到很好的利用。例如跳台滑雪,一般运动员都要经过15~20年的辛勤训练,从一个90-140米巨大落差的跳台上起跳、助滑,以80-90公里的时速加速,腾空,再落地,是一项融合了速度、力量和勇气的极限运动,运动员的身心突破极限均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训练,可以说相比普通人,这些运动员都是“超人”。

▲“超人”跳台滑雪运动员在助滑道上,关节和肌肉所处的状态和常人进 行步行活动、爬楼梯和登山活动的对比
给“超人”用的竞赛设施,如何能在赛后以某种方式为常人服务? 以前的冬奥会举办国,特别以欧美为主,他们的投资主体和赛后运营主体以及赛事举办主体是相互分离的,因而很难把赛时和赛后的利用作为总体系统去考虑。而我国因为独特的公共治理体系,这个系统的整体考虑则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本届冬奥会从一开始,规划和建设就采用了跟以往完全不同的理念,即设计之初就根据国情,为场馆所在地的赛后民生做了设计。那么,如果想把赛时的“超人”场馆融入赛后的常人生活,我们需要考虑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首先,人们在相对比较亲密的环境里需要共享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里可以有不同的空间布置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活动,我们管这个叫“共享任务”——灵活的空间组合产生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其次,如果范围扩大一点,比如两三百米到四五百米,人们去散步、漫行、步移景异,这个是“漫游任务”,可以获得游历的体验。
再次,把时空再扩大一点,比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或者雪后的颐和园,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去度过半天时间或者一个周末。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些地方当成目的地,这就是一个“目的地任务”,可以给人们留下完整美好的体验记忆。
另外,很多在城市里或自然环境中有相当辨识度的建筑,建成后它会成为这里的代表性建筑,这个是形成文化的标识性,是一个“识别性任务”。
我们把这四个“常人任务”融入冬奥比赛的“超人任务”的设计中,让这些场馆在赛后可以比较好地服务于普通人的生活。这样的结合,让冬奥的场馆建筑突破了“白象”问题的瓶颈,让冬奥场馆获得更好的可持续性利用。
那么,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在我们行业内,目前可以通过人因技术来完成。通过收集人的一些生理信息,比如在观察环境时对人的眼动进行追踪,和他所在的时空位置结合起来,经过耦合即形成一种叫做人因分析(从人的因素出发进行的分析),从这个分析可以了解到,人和环境的互动以及对环境空间的审美和体验强度。
戴上有眼动信息收集能力的虚拟现实眼镜,可以在建筑建成前就实现相关的人因分析。通过人因分析技术,我们可以验证常人任务能否合理地在竞赛设施上体现。同时,在一些精细之处可以通过枚举法实现设计的选择和优化。
❄ ❄ ❄
相约“如意”:设计灵感来自S形曲线
跳台滑雪是一项非常令人崇拜的运动,因为它需要克服常人都有的恐惧心理,运动员训练大多从小时候开始,从20米落差的跳台逐渐增加到40米、70米,再到90米的比赛标准。跳台比赛最关键的一个是运动动力学上的特征:运动员从助滑加速到腾空飞行,再到逐渐落地的一条曲线。因此,竞赛跳台设施要保证运动员腾空以后,在不超过3米到3.3米的情况下,有一个面永远能够承载他。这条曲线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运动员飞行曲线的一个位移。
本届北京冬奥会使用的跳台,一个是标准跳台落差在106米,一个是大跳台落差在140米。因为跳台落差大,山谷环境里出现一条巨大的S形曲线的时候,大家会把它认为是非常可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完成跳台竞赛这样一个本身的超人任务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常人的识别性任务可以很好地结合,因为跳台设施本身就有很明确的显现度。
既然是在中国办冬奥会,冬奥建筑既要承载这个S形曲线,也应有中国的文化元素在里面。我们找过圈椅里头的扶手,博古架上的彩云图,剑鞘、玉带配钩等。后来发现S形曲线在我国文化里头最易被识别和接受,且含义非常吉祥的就是如意。
我们把如意的形象转译到和相应的跳台比赛设施里可以看到,柄身部分完全可以承载两个赛道,而柄尾部分可以作为运动员落地以后那个观众聚集的结束区。但如意柄首部分是以往的跳台滑雪中心设施都没有的。

如果把一个如意的形象能够用大家接受的,并且在山体里看起来相对优雅的比例建造出来的话,经过估算,柄首部分至少得有80米的直径。我们和国际雪联的竞赛部主任瓦尔特·霍费尔确认,在跳台出发区设计一个80米直径的顶峰空间是不是可以。
当时他沉默了10~20秒,当他沉默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紧张,因为如果他说不行,作为竞赛刚性要求不能满足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放弃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了。
结果,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可以,虽然以前从来没有做过80米这么大的出发区——以前最大的是在1964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奥会上,有一个能够站10~20个运动员的小的步行桥。这次做到直径80米,可能在跳台的顶部将来会形成一个有人气的场所,这对解决跳台的长期利用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样我们也就有了今天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雪如意”。

“雪如意”的柄身部分有两个侧翼,这是做什么的? 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最不希望的就是侧向的风。侧向的风会把他们吹离承接面部分的赛道,会非常危险。
索契冬奥会和平昌冬奥会布设了数百米的防风网,防风网成本高昂,对环境也有很大影响。索契冬奥会用了 400 米,平昌冬奥会用了近 700 米,北京冬奥会因为有了如意的两边侧翼,仅在山脊肩膀背侧增加了100余米的防风网。
我个人也去跟运动员访谈,去问到底怎样的场馆会使他们的印象深刻。我了解到,运动员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找风和飞行上,但出发时刻大概有0.3秒的时间,他们会观察周边景物,留下对周边景物的印象,对运动员的心理状态产生很大影响。过去几届冬奥会,最受欢迎的是温哥华冬奥会的惠斯勒跳台,因为对面有座印第安神山,飞向印第安神山会对运动员有正向刺激,可能也会让他的表现得到提升。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利用好这0.3秒?我们把北京冬奥会跳台原来的朝向——由国际雪联跳台建设委员会主席汉斯?马丁先生根据地形计算出的最小开挖量的方向,往北旋转了20度。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人的水平视角是45度,按照汉斯·马丁先生原来的计算,运动员是对着对面的小山包跳下去。旋转之后运动员是对着东侧山谷跳下去,而山谷尽端的山脊上是明代长城的遗迹。同时,我们也发现人们在参观“雪如意”在顶峰停留时,都会驻足远眺长城,这种正向刺激是具备普遍性的。

“雪如意”另一个要完成的是“目的地任务”。想要让建筑和它周边的景物成为文旅目的地,必须要提供2.5小时的慢行和驻留体验。
在冬奥会比赛中一般有一个被称为北欧组团的场馆群,就是北欧两项运动(跳台滑雪加上越野滑雪),再加上冬季两项运动(越野加射击,源于原来的军事训练),这几个项目的场馆组团,对赛后利用来讲,实际是做成一个单位去营造一个吸引力。我们想办法在组团里面完成目的地任务,因而除了竞赛设施以外,我们附加做了一个供人慢行的步行桥——“冰玉环”。环形建筑最早是一个瑞士团队提出来的,他们建议在小山包修一个像苹果公司那样的五层综合体,把酒店、场馆都修在那里,这是很浪漫的设想。不过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环状的提出,把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三个场馆联结在一起,提供2.5小时的慢行和驻留体验。
我们为此专门采用了一个结合人因技术的工具,叫做城市人因量谱图。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和可穿戴设备,我们可以通过穿戴设备所收集的人的生理信息、心理信息和环境空间进行耦合,判断出人和环境之间交互的强度,因而可以相对准确地预测出:特定空间下,用虚拟现实的办法模拟出这个可能性,再用实测数据反馈回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基准的,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关系底下可能产生的人的驻留时间,并且以这个为基础再去测试建成以后实际的人的驻留和环境互动的强度。
依据这种测算,北京冬奥会的北欧组团可以提供约185分钟的慢行驻足时间,而平昌是75分钟。
❄ ❄ ❄
冬奥场馆:服务“超人”更服务“常人”
在人因技术的支持下,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不仅为竞赛服务完成“超人任务”,同时,更服务于常人。
在整个张家口赛区进行慢行系统规划时,我们要对山体进行多多少少的修改。这样被切削的山体进行有机修复之后,可以形成赛后步移景异的慢行体验。
这里用到的技术不是国际上常用的用混凝土做护坡,然后再用石龙香去种植,最后形成几何形状的山体的绿化方式,而是一种完全有机的绿化。这个技术来自于我国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借鉴了煤矿矿坑修复时用的技术。这种技术非常聪明,用一种编织的网先固定少量的土,毛茸茸的草长出来后,能够固定更多的土,然后可以长更大的植物。经过这样修复的山体,会形成植被丰富的地表状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准自然的修复方式会让山体的植被更好地呈现。
再看“雪如意”,建筑本身也有对漫游任务的一种特殊关注。以前举办过冬奥会和世界锦标赛的跳台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陡峭的跳台是普通人不易接近的。从利勒哈默尔到惠斯勒,再到平昌到盐湖城,跳台只能远观,不可亵玩。
而对人的体验来说,什么地方不能到达,我们就不把它算在空间拥有亲近体验的范围内,建筑就造成了疏离感。以前跳台的设计,仅为比赛修复雪面的工人留了一侧附加台阶。这次我们特意把两个跳台的四个边,中间的两边最后在底下合成一条线,全部修上了台阶,这个台阶在大跳台的一侧有700多级,在小跳台的一侧有600多级。人们就可以连续地从下面的体育场走到上面的顶峰俱乐部,也能从上面的顶峰俱乐部再走下来,形成一种登山时候到了一定阶段回望一下,看看景色的变化,拍拍照,聊聊天⋯⋯这样的慢行体验可以在整个跳台里完成,跳台不再是跟人疏远的建筑,而是能亲切体验的建筑。

再看一下“漫游任务”之后的“共享任务”。上面的顶峰俱乐部是一个中空的环状空间。它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体验,就是在内环里可以直接看到跟运动员出发相同方向的视角,这个视角在电视转播中被称为跳台出发的黄金视角。等于在室内环境里,就可以直接和运动员有这样一种互动。

我们看看图中A和B两个室内的空间,A空间主要用于前面的观景,B空间大概能够达到900平米左右,没有任何柱子,可以完全作为多功能的活动空间,这是典型的一种共享空间。从展览到会议演出,到文旅餐饮,甚至有人提出可以在这举办婚礼。我们期待这样的空间能够在赛后很好地完成共享任务。据我所知,很多大型企业已经在预订“雪如意”的顶峰俱乐部了,这块顶部空间有望在下半年举办一些大型活动。
底下的体育场也是一个特殊的共享空间。传统的跳台滑雪比赛里,体育场的空间一般是一个反坡,这样运动员可以快速减速。但观众席必须全部45度方向斜向地朝向跳台。这样设计的体育场空间就不能作其他用途,仅能用作跳台滑雪比赛。正因如此,挪威奥斯陆的滑雪跳台,最后不得不干脆在夏季接水,让它变成一个人工湖。为了冬奥场馆赛后的可持续利用,我们坚持做了一个90米的平坦空间,一个国际标准足球场里的最小尺寸,让11000名观众仍然环绕在这个体育场周围,这样就可以让其他户外活动也在这里进行。这样一个体育场,已经在2020年12月份得到了一次多功能使用的验证,河北省冰雪运动会的开幕式就是在这里顺利举行的。
❄ ❄ ❄
“飞天”亮相:首钢选址诠释可持续发展
滑雪大跳台项目拥有冬季雪上运动里唯一偏向城市的粉丝群体,一般在城市广场举行。这项运动由运动员加速助滑、起跳、腾空——腾空高度有时接近15米,比跳台滑雪运动腾空高度高很多。空中翻滚,然后落地,很惊险,其实属于雪上极限运动。
以前,滑雪大跳台倾向于在城市中心广场修一个赛后拆掉的临时建筑,很费钱。城市的粉丝群体听着摇滚乐,喝着啤酒来看比赛,就是一个大型派对。
而这次北京冬奥会选址的时候,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贡献——提供了首钢工业园这样一个工业遗产的背景,比城市广场还要酷,所以基本上一拍即合。当首钢工业园内的冷却塔和奥林匹克场馆结合在一起,简直是国际奥委会向国际社会说明,奥林匹克运动是怎样完美融入和参与地方城市中心的最好论据。

所以,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结束之后,首钢滑雪大跳台也将成为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它将继续保留比赛及训练功能,并面向公众开放,实现它的新价值,这也是设计伊始就考虑到的问题。
滑雪大跳台运动的英文名字是Big Air,就是最大限度地向空中腾跃,我们可以理解为往天上飞,飞天。所以,敦煌飞天形象里的飘带就是最初设计灵感的来源。
最初,这个飘带设计只有一根,而且怎么也“飞”不起来。我们设计团队里一位学过珠宝首饰设计的年轻设计师,她提出一个想法:想要飘起来,需要几条曲线缠绕在一起。正好跳台下还有一些临时竞赛管理和运营设施,需要吊挂一些结构,就有了第二根“飘带”,有了它以后,整个情况就变得好多了。但是还有一点不那么满足的地方,运动员上到顶端出发时以及上面的转播平台四面都是漏的,如果再用一根彩带包进来,就有可能让飘带飘起来更舒服,然后就形成了现在这个首钢“雪飞天”跳台的形象。
建筑识别性除了它本身的跳台以外,我们还必须把它放到工业遗产环境里来看。我小时候在北京长大,曾去首钢学工。冷却塔后面是西山,前面是冷却池的画面,形成了一个天际线,怎么在加入一个新跳台时不破坏天际线呢?

我们再一次用到了城市人因技术。在风和竞赛、朝向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概50度左右的范围里做了10组测试。测试方法是,被试者在虚拟现实环境中,从冷却池现在叫做群明湖的东侧树后走出,这时天际线呈现出来,然后测量被试者眼部观察到的内容和相应的皮电数据,就能知道这样的场景对他起到的唤醒程度,以及他对唤醒持有的正向或负向的刺激。测试结果表明,被试者认为有天际线能够被认为是一个整体,被试者对跳台本身和冷却塔关注程度比较均衡,同时,跳台建筑本身也给他带来了更多愉悦性的刺激。
当然还有在长安街延长线上看跳台的问题,这个更多是从视觉上用它和周边景物的融合感,比如跳台不能在视觉感知上比冷却塔高,所以跳台结束区就需要沉到湖面以下5米。比如跳台有斜行的电梯,但是它的角度和冷却塔接地角度有类似对称关系。
运动员比赛时,经过冷却塔上映出来的影子,经过斜行的电梯上到出发区,从电梯走出来,整个首钢园区就在底下,远处城市尽收眼底,这是很兴奋的起跳心态,对观众来说也是一样,冷却塔永远是观看这个当代城市比赛项目的一个背景,特别是在夕阳西下时非常美。在这里参加过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的选手表示,大跳台给人以梦幻般的未来感。

“雪飞天”特殊的工业遗产环境,还吸引了国际雪联的技术专家做了一个他们以前从未做过的决定,就是把经常在山地里进行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和滑雪大跳台项目放在一个地方完成,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两个项目的竞赛曲线差别很大,但是为了首钢工业园这个有吸引力的场景,两位国际雪联的专家,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的赛道设计师大卫和空中技巧滑雪的赛道设计师乔,一起到首钢项目长期做设计的比利时结构工程师、建筑设计师戈建家的四合院里头,喝着啤酒完成了设计图。结构工程师杨霄老师进一步完善设计出了正四面体结构模块,模块可以附着在大跳台的系统节点上,48小时之内就可以把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的曲线转化成空中技巧项目的曲线。

这个变换技术是全球首例。但很遗憾,因为疫情的原因没能够在2020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得到实现。北京冬奥会比赛也已经确定,但未来的比赛,完全可以通过附加临时单元体结构在48小时内完成向空中技巧场地的转换。
对于目的地任务来说,首钢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首钢整个园区的改造非常精彩,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看漫游任务是怎么完成的。首钢的群明湖周边,环绕湖区的景观和设施要怎么安排,才能够让人获得最好的体验?能不能借鉴一个已经有的,大家公认留下美好记忆的湖呢?
我们选择了比群明湖大4倍的颐和园昆明湖。我们学院的朱育帆教授做了湖岸线改造,张昕教授做了照明改造,同时采用虚拟现实中眼动追踪的办法,看到人在宽阔水面的边界行进时,注意力角度的变化和相应远端景物对人形成节奏的影响,把颐和园的拓扑关系复制到首钢的环境里,这样就能够让人在环湖路径当中形成类似的节奏感,让人关注到一些重点景物的出现。人经过芦苇荡这种起起伏伏,又可以通过水面下景观的步道走到水里,体验这个空间,这和颐和园盘云殿底下码头的设计类似。环湖走到罐区又有一个停留节点。北面还有由吴晨教授设计的,把首钢原来的管道变成一个首钢新的高线公园,目前是这些游客们家庭活动、亲子活动、慢跑活动的场所。

接近跳台的结束区还有一个小的制氧厂区,这里的十几栋建筑完成了最后的“共享任务”。我们请首钢的老工人们来投票选出来他们最希望留下来的工业遗存,遵照原来的机理来改造新的厂房,把它变成一个创意街区。其中最大的厂房我们请到了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团队,他们参与过著名的米其林工厂改造。据我所知,赛后这里已经被一些文化和体育产业的企业预订作为创意办公空间了。
总体来看,冬奥场馆建筑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仅是一个办赛设施的意义。我们用到了一些创新技术,当然最主要的是借助人因技术,对赛后设施的利用和空间需要有的形态进行更精准的推断,让冬奥场馆在赛后能够真正服务于民生,服务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整个北京冬奥会的筹备中,我们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讲述了中国故事,同时也在为奥运遗产的规划和使用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相信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顺利举行,将会有更多筹办成果转化为冬奥遗产,不仅造福广大人民群众,也为城市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长期收益,在奥林匹克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
(本文内容来自2022年02月19日的首都科学讲堂。讲堂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北京科学中心承办、北京科技报社协办,每周邀请院士专家开讲,弘扬科学精神,帮助公众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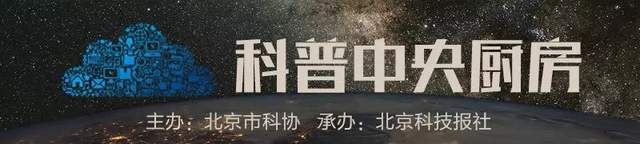
出品:科普中央厨房
监制:北京科技报 | 北科传媒
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帮助
帮助
 北京科技报
北京科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