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九江,庐山犹如一座天然的堡垒,耸立于长江之畔。1938年,当战火席卷江西,这座高山成为战略要地和避难之所,而庐山植物园也随之卷入历史的洪流,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岁月。

一棵树的抗战:百年杉廊里的"气节树"
在植物园百年杉廊,一棵形态奇特的柳杉静立林中。它比周围树木矮小纤细,中段枝杈丛生,这独特形态背后,藏着一段悲壮往事。
1938年,日军对庐山实施轰炸。位于含鄱口的"太乙十八将军村"因电台信号频繁,成为重点攻击目标。毗邻的植物园未能幸免,一枚炸弹在这棵柳杉附近爆炸,弹片将其拦腰削断。
树木自有求生之道。为弥补光合作用的损失,这棵柳杉不得不萌发新枝,向四周伸展侧枝。随着周边树木不断长高,为争取阳光,它奋力抽出一条新主干,向上突围。这顽强生长的过程,恰如毛泽东《论持久战》所阐述的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
如今,这棵"气节树"已成为活着的抗战纪念碑,见证着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的坚韧品格。

(百年杉廊里的“气节树”)

(“气节树”树干有一部分没有任何分支,是其不断向上生长,争夺阳光的痕迹)

(远远望去,“气节树”(中间)明显要低于左右两边)
丽江工作站的建立
1934年创建的庐山植物园,至1937年已收集3万余号珍贵标本,包括大量模式标本和珍稀物种,是中国植物学研究的核心家底。
战争阴云逼近时,植物园做出了艰难抉择。1938年夏,在秦仁昌主任带领下,员工将标本、图书及科研资料装箱寄存于庐山美国学校,随即开始南迁。
他们选择的落脚点是云南丽江——这里植物资源丰富,利于科研延续。1938年12月,庐山森林植物园丽江工作站正式成立。在经费断绝的困境中,科研工作仍未停止:秦仁昌继续蕨类植物研究,1940年发表《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震动国际学界;冯国楣等人赴中甸、玉龙雪山等地采集,获标本六千余号、活植物八百多种,发现大量新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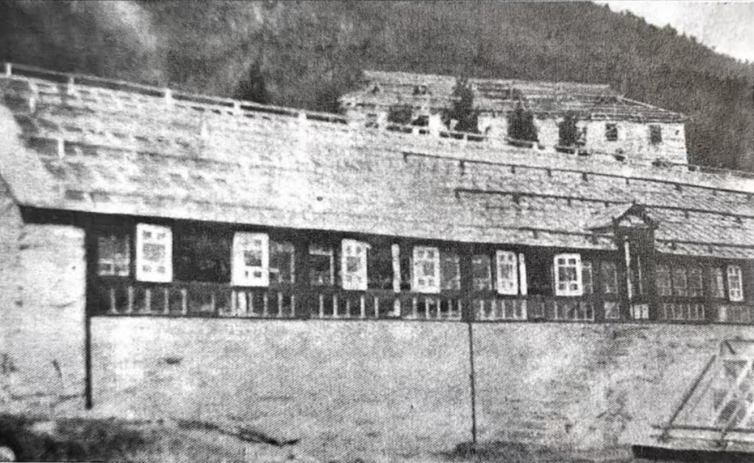
(1938撤离之前的庐山森林植物园。前为温室,后为尚未竣工的森林园艺实验室)
为维持运转,科研人员甚至试制松香、办厂生产,以科学支援抗战。在丽江期间,他们共采集标本两万余号,为战后中国植物学重建保存了实力。

(这是从美国远道运来的桶装水泥,原本用于庐山植物园的建设。然而,尚未等到投入使用,植物园便在日军的侵略中沦陷。待到抗战胜利,工作人员从丽江复员归来时,这两桶水泥外层的木桶早已腐朽,其中的水泥也早已凝固成块。如今,它们静置于植物园一隅,作为一段无言的往事,沉默地见证着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战火中的坚守与复建
当大部分人员南迁后,植物园原址遭受了严重破坏。1938年,在其他领导先期撤离的情况下,陈封怀坚守岗位,直至听见炮声才被迫离开。
1946年,陈封怀教授返回庐山,主持植物园的复建工作。面对满目疮痍,他兼任中正大学教授,用授课所得贴补植物园支出。1948年,面对强行挖掘园内树木的要求,他坚守底线,坚决保护植物资源。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与职工临危不退,保住了中国当时唯一的植物园。
如今园内仍可见日军轰炸留下的弹坑,其中放置了炮弹模型,以此警示后人,铭记历史。

(庐山植物园内日军弹坑之一,目前在坑中放置了一枚炮弹模型,以警示后人,铭记历史)

(庐山植物园内弹坑之二,后人用石头环绕,里面杂草丛生,自然的力量终将愈合土地的疮痍,但战争留下的历史伤痕,却难以抚平。)
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八十载光阴流转,百年杉廊里的"气节树"愈发挺拔,新枝比老枝更加茂盛;弹坑边的南天竹长势旺盛,结出丰硕果实;那两桶从美国运来、未来得及使用的水泥,早已凝固成块,静置园隅,默默见证着那段历史。
庐山植物园的抗战记忆,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在和平的阳光下,开出最美的花朵。这里每一株植物都是一个故事,每一寸土地都有一段历史,诉说着中国科学家在烽火中守护文明火种的不屈精神,见证着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未曾放弃的科学理想。
这段历史不仅属于过去,更照亮未来。它告诉我们: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知识和文明的种子也永远不会湮灭。
来源: 植物界LSBG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帮助
帮助
 植物界LSBG
植物界LSB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