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至蓝鲸、小至病毒,生物世界千差万别,但无论形态多么丰富,它们生命的奥秘却都藏在微观结构之中,比如体内蛋白犹如构筑生命大厦的砖石,决定着生命体可能具有的功能。而若要将蛋白质结构探得明晰,必须走入“微观”。不过,对于探究微观世界的手段,尤其是原子、分子级结构的研究,自光学显微镜的性能开发几乎摸到“天花板”后,科学家的摸索横跨了以世纪为单位的时间,这一僵局最终还是被冷冻电镜的出现所打破。
作为一项颠覆性新技术,冷冻电镜可以让科学家看到许多悬而未决问题的背后机理,让细胞中模糊的斑点逐渐清晰。“这就好像为细胞、蛋白等微观物质做了个‘CT’。”投入冷冻电镜技术研究数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助理教授、科比尔卡创新药物开发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红丽已经可以深入浅出地将晦涩的原理进行类比。多年来,她始终坚守在基于冷冻电子显微镜的膜蛋白结构研究岗位之上,不仅曾与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K.科比尔卡(Brian K. Kobilka)教授和罗伯特·J.莱福特霍维茨(Robert J. Lefkowitz)教授开展多项合作研究,且在多项重要G蛋白偶联受体(GPCRs)的结构研究中均有重大突破,其中多篇科研成果已发表于《自然》(Nature)、《细胞》(Cell)等学术期刊,获得国际广泛关注。

▲胡红丽
2019年,学成归来的胡红丽正式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科比尔卡创新药物开发研究院担任独立课题组负责人。在她与先辈、同仁的努力之下,冷冻电镜技术在今天已经逐步走向了大规模应用,G蛋白偶联受体背后奥秘相继揭开也为某些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这无疑为结构生物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即从平面到立体的跃迁。
以“镜”制“冻”,走进微观
简单来说,冷冻电镜就是将蛋白质保存在非常薄的液体层中,然后将它们冷冻。仪器以高速电子束为光源,对蛋白质进行成像。它有着两项强大功能,一是“万物皆可冻”,只要有需求,不论是生物组织、病毒还是大分子等,都可以通过冷冻电镜观察样本;二是通过冷冻电镜的三维重构能力可以很好地观察到样本的内部结构信息。
这些前沿的技术与知识第一次出现在胡红丽生命中,是在她大学三年级的学术讲座上。最初,“想学应用性专业”的理想将她带入了南开大学应用物理系。本科前两年的物理学基础课程,也的确让她积淀下了深厚的专业知识,但她始终很清楚,自己的梦想在于做研究,以所学切实改变生活。此时,她的人生“引路人”——尹长城教授携带着冷冻电镜与生物物理学,走入了她的视野,也由此改变了她的职业轨迹。
“冷冻电镜在微观世界的应用刷新了我的认知,尹长城老师深入浅出、声情并茂的讲述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并蓄吸纳着拥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年轻人。在他眼中,每个相关学科均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例如物理,可以帮助我们快速且透彻地理解仪器背后的工作原理,从而精准挖掘仪器的应用潜力或直接提升仪器的参数与准确度来突破现有的研究困境等。他坚信,未来的科学研究一定属于交叉学科。”前辈巨大的人格魅力与深厚的学术造诣也在之后的岁月中持续吸引着胡红丽,使她坚定地跟随导师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物物理学系接续深造。
虽然在整个博士阶段,胡红丽始终认为自己做出的成果还未达到自我要求的标准,但她还是盛赞这一时期为“对职业发展最有帮助的阶段”,她说:“读博期间最主要的就是把关于冷冻电镜的原理、成像技术和图像处理、应用相关知识都掌握透了,这无疑为我如今的科研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2008年入行,胡红丽见证了冷冻电镜研究新时代的开启与疾速腾飞,“每天都在见证冷冻电镜的突破”。这一时期,软件和硬件方面的改进,使得冷冻电镜各个方面的性能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一方面,分辨率的极限一直在被打破,业内称其为“分辨率革命”(resolution revolution);另一方面,冷冻电镜的研究对象也向分子量更小的蛋白质进军,越来越多的蛋白被证明可以通过冷冻电镜解析。2017年,雅克·杜波切、约阿希姆·弗兰克和理查德·亨德森3位科学巨匠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也再次将冷冻电镜在微观领域的突破推向发展的风口浪尖,而彼时的胡红丽,也已走出国门,远赴他乡,开启了自己人生中的研究新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出国的6年时间里,胡红丽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留下了自己奋斗的印迹。“在海外我接触了许多业内领军人物,如斯坦福大学有30多位诺奖得主,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跟他们面对面聊科研甚至生活,跟他们学习如何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胡红丽成为许多正式或非正式学术活动的“常客”,每到周五下午,她总会选择与三五好友围坐举杯或是阔步高谈。她形容大家总是“三句话不离自己本行”,就连偶然吃到一种口味独特的蔬菜,他们都要对其中分子“追本溯源”,如果一时难以得出定论,还要回去翻阅文献,“科研源于生活也将惠及生活,说不准崭新且极富价值的研究方向就藏在身边”。胡红丽说,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研究就在这一阶段正式走入了她的视野。
燃灯前行,勇攀高峰
无论是在药品说明书上还是生物教材当中,G蛋白偶联受体(GPCRs)都是频繁出现的一个“大家族”,因为市面上有大约30%的药物都是通过作用到这类蛋白上才得以发挥作用的。但跟随导师乔治亚斯·斯基尼奥蒂斯开展研究并加入其课题组之后,胡红丽却发现原来科学界对GPCR的认识仍然非常有限。纵使已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业界对GPCR的结构了解也不过“十之一二”,对于大部分GPCR的结构探究仍属一片蓝海。“这就好比我们要开一把锁,却连锁芯构造都不清楚。在无法精准开锁的情况下,只能手握一堆钥匙去依次尝试。”本质上讲,其实根本桎梏在于晶体学的结晶难度——GPCRs作为膜蛋白,想要找到它们的结晶条件,难度可比大海捞针。但巨大挑战背后往往蕴藏着高收益或是大突破,于是,胡红丽所在的课题组毅然选择燃灯前行,勇攀学术高峰,尝试用冷冻电镜解析GPCR复合物的结构。
“那几年里,我和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K.科比尔卡(Brian K. Kobilka)教授多有合作,取得了好几项突破。”胡红丽说。而这些工作中令她最满意的是有关Class C的结构研究。这项成果极富代表性,原因在于Class C GPCR和其他类型GPCR差别很大。“所有的GPCR都有7次跨膜螺旋,但Class C GPCR在胞外有个很大的结构域,且它的正构位点不在7次跨膜区,而在胞外的结构域上。我们研究的代谢型谷氨酸受体5(简称mGlu5)是参与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突触传递和神经元兴奋性受体,一般是以二聚体的方式行使功能。”胡红丽适时补充,“这个工作是我在密歇根大学的时候开展的,我一边测试样品,一边测试自动收集软件。刚开始的时候,在薄冰中找不到蛋白颗粒,只能在厚冰处收集数据,图像衬度比较差,分辨率也很难提高。后来我们改进了制样技术,把蛋白质冻到很薄的冰层中,图像衬度就有了很明显的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红丽的研究工作发表之前,C类GPCR的相关机理并不十分明确——即便使用全长的分子进行结晶得到衍射也无法计算出跨膜区结构,同时亦无法得知配体结合到正构位点之后是如何传递到跨膜区的。但冷冻电镜却再一次为这些困局注入了新的活力。胡红丽所在的团队解析了mGlu5在失活和激活状态的两个结构,即失活状态胞外VFT(捕蝇器)区域是张开的,二聚体也是几乎平行的;配体结合之后则被VFT捕捉,而后VFT关闭,带动二聚体产生较大位移和旋转,跨膜区距离也随之变短,7次跨膜的构象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也获得了《自然》(Nature)杂志的青睐,在此成果发表的同时,《自然》杂志在同期的“News & Views”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近距离观察激活的受体(Excitatory receptors in close-up)”的简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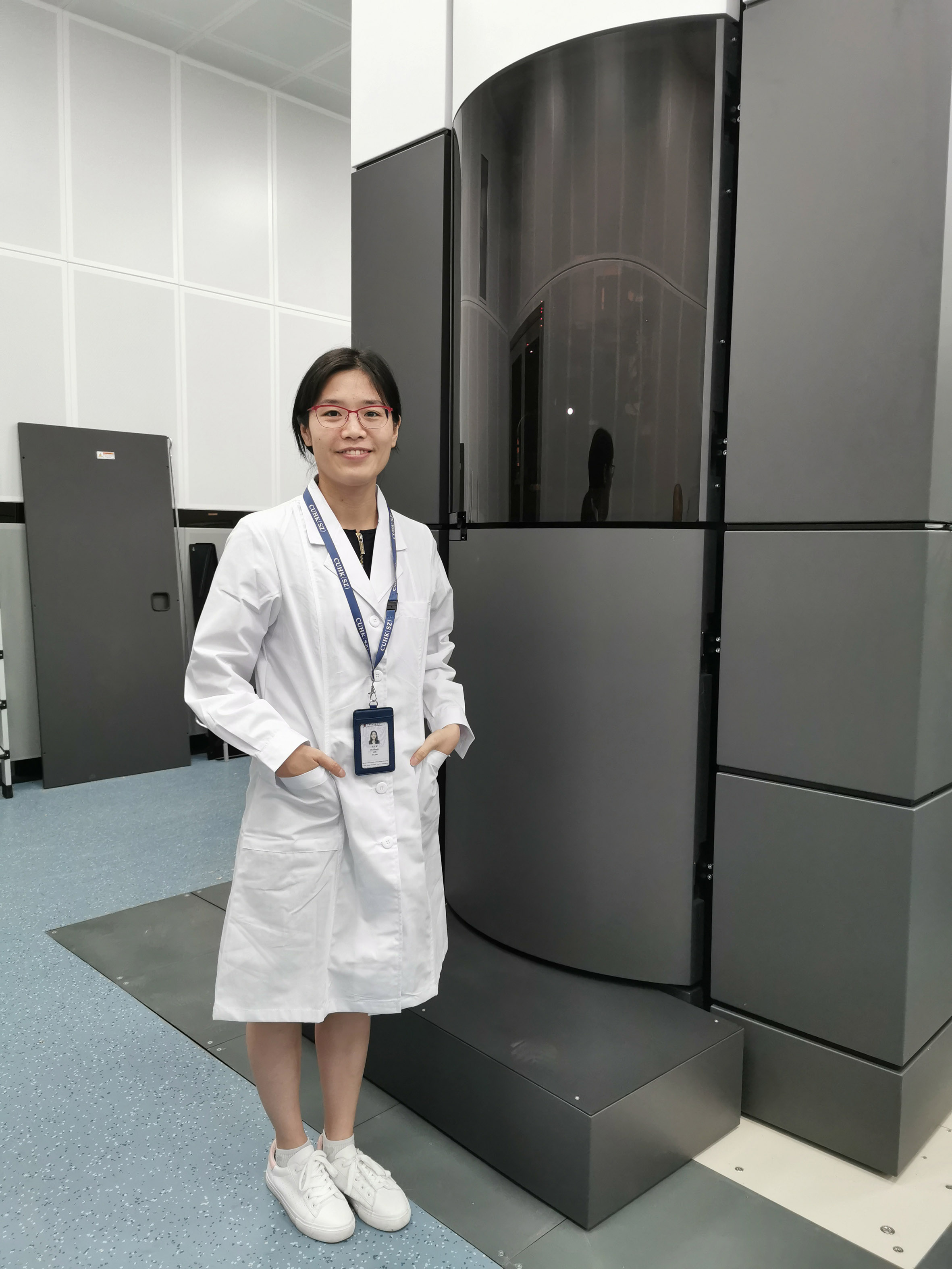
▲胡红丽在科比尔卡冷冻电子显微中心
此外,胡红丽另一项为人称颂的工作是和GPCR的领军人物罗伯特·J.莱福特霍维茨(Robert J. Lefkowitz)合作研究的,他曾和布莱恩·K.科比尔卡(Brian K. Kobilka)教授一起斩获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相比于GPCRs和G蛋白的关系,GPCRs与阻遏蛋白的结构关系更加鲜为人知。即使到今天,我们获得了上千个GPCR的结构,其中只有不到十个是关于阻遏蛋白的。”胡红丽如此阐述这一研究得以开展的背景,而在探索这个复合物的过程中,她也因为其不稳定性吃了很多苦头,直到尝试过几十种不同的实验条件,采集了几万张图片,才终于在冷冻电镜下捕捉到复合物的一个稳定状态,最终解释了阻遏蛋白的招募过程几个关键的科学问题。而功不唐捐,最终这项成果也被《自然》(Nature)杂志接收。
上述所有研究成果的问世为胡红丽的海外研究生涯交上了高分答卷。羽翼渐丰的她很快产生了强烈的归国想法。“是时候将自己的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了。”她说。行胜于言,很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迎来了一位出色的新成员。
以我之力,追我所愿
以力争站在世界药物研发科学前沿为总体建设目标;以“注重源头创新,关注科学核心问题,与革命性技术与产业化战略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以“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做出高端成果,同时将深圳学术研究带入世界高水准”为期许,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科比尔卡创新药物开发研究院(简称“研究院”)在成立之初,便吸引着胡红丽的目光。基于对平台的向往,她甘愿接受“从零开始”筹建实验室的挑战。
“当时实验室内没有任何设备,无论是需要自己建立复杂的实验室系统,还是亲力亲为开展人员招聘、人员培训等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一套陌生的流程。不过幸好,通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实验队伍已经初具雏形,可以系统地完成GPCR结构的解析工作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的首个着力点——炎症趋化因子受体的探究才有所进展。
炎症趋化因子的作用靶点(趋化因子受体)表达于巨噬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细胞表面,属于GPCR家族A类成员。目前学界已明确鉴别出约20种趋化因子受体和约50种内源性趋化因子,在多种疾病治疗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趋化因子受体如何调节免疫细胞功能的分子机理却仍属未知,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靶向趋化因子受体家族成员的药物也只有3种,仍存在严重缺口。
因此,胡红丽团队选择了炎症趋化因子受体CXCR3作为切入点予以破局。依托于相关项目,胡红丽团队获得了多个不同配体激活下CXCR3的结构,发现了配体不同的激活模式。同时他们也捕捉到正构和别构抑制剂的调节位点,“把控制CXCR3开放和关闭的每个机关都找到了”,这些结构将为我们设计新的机关密码,为相应疾病的治疗提供指导。目前相关工作已有两篇文章被自然《自然》(Nature)子刊发表,未来仍大有可期。
关于未来的打算,胡红丽始终头脑清晰、态度坚定:“我知道未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且可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然而,我对自己和我的团队充满信心。当逆境降临,我们有能力制定出卓越的应对策略,共同克服困难,迎接每一个挑战。”
来源: 科学中国人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帮助
帮助
 科学中国人
科学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