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维坦按:
不知怎的,看这篇文章总想起诗人布罗茨基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手的意向,比如“福图内斯特,我想住在一座城市里,那儿会有一条河从桥下伸出,如同一只手伸出袖口,然后流向海湾,展开它的手指”(《阐述了的柏拉图》,王伟庆 译),“像一行诗那样,落下的灰尘对拿着布的手悄悄地说:‘不要忘记我‘,而那块湿布吸走了这句话”(《特尔斐以北》,王伟庆 译),“为那只从来没有抚摸过钱的手,更不用说去摸一个创造生命的器官”(《里斯本来的明信片》,王伟庆 译)。
想想也是,人的手一生中会触碰无数的事物——作为一个行为动作的执行端,手连接了人与这个世界,这里面既有时间上的连续性神圣/日常想象(比如擦完屁股后的手开始翻祈祷书页),又有空间上延展与形而上规模(比如手与命运和宇宙的关系)——这么一想,可真是神奇啊。
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有一块14世纪法国的小象牙匾。匾牌很小,只有5厘米宽、8厘米长,小到可以整个放进手掌中。它原本可能是作为书写板用。还有一块大小相同的匾牌与之成对,它们原来应该是铰接在一起的,像微型书本一样,匾牌有雕刻的那一面犹如书本封面,而其反面的凹陷空间则覆有一层薄薄的蜡涂层。
匾牌的持有者可以用刻蜡用的尖笔在凝固的蜡涂层上记录下他们的想法或一些数据,然后把“蜡页”置于蜡烛上融化、重置,就像中世纪的“蚀刻素描”画板(Etch-a-Sketch)一样,轻轻一晃就把字迹清除干净。
匾牌正面用作装饰的雕刻画则能留存许久。它描绘了一群男女紧紧挤在三个壁龛前。这些人形举止优雅——有的站着,有一位坐着,还有两位在地上——正在玩一种在中世纪时被叫做“热蛤”(Haute Coquille)的游戏,有时也叫“热手”(La Main Chaude),这个活泼的名字掩盖了这一消遣的性感本质。
玩的时候,其中一人被蒙上眼睛,然后被打屁股。在大英博物馆的象牙匾上,一个年轻人正跪在人群中央,脑袋埋进一位坐着的女性的裙摆褶皱里,这样他就看不见(是谁在打他)了。
尽管作品尺寸很小,年轻人的轮廓还是精致地刻画出来了,幽灵似地出现在布料下,并且我们从他的手部轮廓中感受到了游戏潜在的色情之处,因为他的手正沿着女人的左大腿向上摸索。打屁股的动作则能从他身后两位女性举起的右臂上看到暗示,她们的手被夸张地描绘出来,正要挥打到他臀上。
游戏结束时,被蒙住眼睛的人只能靠被打的刺痛感来猜测打他/她的人是谁。如果他们猜对了,他们将得到一个吻作为奖励,可以看到,在象牙匾的右上方,一对胜者夫妇正在壁龛之间悄悄地拥吻。
在这幅作品中,人们的手很显眼。他们触碰、挥打、轻拍、系结、指点、摸索、爱抚、打屁股。我们看得越仔细,就会发现越多这类细节。裙下埋着年轻人的女子将左手放在他的头上,同时右手用一根异常细长的手指指向上方聚集的人群。两个打屁股的人正使劲拽起她们自己的裙子。左下角那个留着胡子的人,不知道是在人群上方还是下方,他似乎在摊开双掌拨开女人堆挤过人群。
就连画面最左边的女人——这个人物太过边缘,以至于在匾牌范围内无法画出全身——也被赋予了一只硕大、挥动的手,塞进了画面的中央。这块书写板想必经常会被置于掌心,而当它如此时,画面里这些关于手的细节理应会引发内外的共鸣:象牙匾不仅向身体末端(手指)传达了触感,还通过图像传达了触觉信息本体。
在中世纪早期的古英语文本中,医疗工具和使用它们的人被直接混为一谈。
中世纪的触觉概念很难掌握,其中满是内在的问题和矛盾。与更神秘、空灵,通过透明射线和振动空气传播的视觉和听觉相比,哪怕是与更易感知的味觉和嗅觉相比,在中世纪,触觉被视为位于一切感官的最底层,五感之基础。
也许这是由于它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同时发出并接受的感官,既不完全主动也不完全被动:在伸手触摸某物时,那东西也不可避免地同时触碰你。这一动作中发生了什么?你是在触摸还是被触摸?或者两者皆是?与甜美歌声的惑人魔力、绝妙气味的柔和飘荡或者视觉上的细微层次相比,触觉的这种不精致显然不够高贵。
然而,另一方面,触摸带来了不可否认的感官直接性,有时也意味着它可以被认作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感觉之一。就像嗅觉、味觉、听觉和视觉一样,在中世纪,触觉被认为是通过身体内流动的活力灵魂发挥作用,它将皮肤表面的感觉信息传回大脑进行认知。
但是与其他感官不同的是,触觉是坚固的、实在的,和明确的。它可以让你直接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周围的世界。当然,与听到遥远的声音或看到地平线上的画面相比,远距离的触碰绝不可能,这暗示着某种令人兴奋的亲近感。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是最重要的感官。
学者们仍旧承认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主张,即,触觉是生活中绝对必需的一种感觉。也就是说,一个有机体在没有其他感官的情况下——或聋或瞎,或嗅觉缺乏,或味觉缺乏——仍有可能存在,但是如果没有任何触觉,则只能认为该生命体从本质上是没有生命的,它必然是死去的。在中世纪,触觉就是以这种方式被用作衡量生命力的基本尺度,它本身被认为是一种诊断原则。
通过对病人躯体进行不同程度的推拉,可以确定他们的疼痛程度,同时,敲击病人躯体的特定位置并倾听特定回声或声音的做法受到推崇,时至今日,医生仍然用这种方法来检查胸部的健康状况。医学权威把手描述为身体的工人,利用它们来测试身体某一部分的硬度——肿胀程度、质地或湿度——对彻底了解每个病人的特定情况大有帮助。医生可以通过手指敏锐地感觉到疾病。
***
在中世纪的看病过程中,对这种治疗性接触的重视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医护人员需要用工具而不是手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怎么办?如果他们需要切开病灶、缝合伤口怎么办?如果触摸因其在诊断中的直接性而被重视,那么在这样一种触觉隔离的状态下照顾病人不就有问题了吗?
为了克服这一点,中世纪的外科医生开始建立一种看待医疗工具的新方式,这种新视角在概念上将他们的器械与他们自己的身体融合在一起。具体说来,诸多作者对探针、剪刀、刀和其他工具进行了探讨,将它们视作操作者之手的直接延伸。
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外科手术”(surgery)这个词的词源中都保留了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该词的希腊语词源是“kheirourgos”,拉丁语词源则是“chirurgia”,这两个词都由“手”和“工作”组合而成。
在中世纪早期的古英语文本中,医疗工具和使用它们的人被直接混为一谈,外科医生和手术器械的术语通常是可以互换的。在后来的中古英语著作中,医学专业人员的语言也被日常的身体术语所吸收。无名指也常常被称为“leche fingir”——演变自古英语中的“医生”(læce)——这既是因为医生通常用无名指调和、涂抹药物,也因为人们认为它的静脉直接通向心脏。
法国外科医生亨利·德蒙得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在其关于皮肤的著作中(他配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插图,是个被剥皮的躯干形象)甚至把他手术刀的接槽和刀片描述成像外科医生自己的指甲和手指一样。
这种语言学的概念也可以反推,外科医生们写道,他们自己需要塑造精细,就像他们精巧的外科工具那样。意大利医生米兰的兰弗朗克(Lanfranc of Milan, c. 1245—1306)强调外科医生需要拥有纤长的手指,而与他同时代的佛兰德作家杨·伊珀曼(Jan Yperman, c.1260—1330)则说外科医生需要“vingheren de lanc sterc van lichame,niet bevende”——“从身体长长伸出、不颤抖的手指”。
当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些外科医生在手术中可能使用的复杂工具,就能逐渐明白他们的话是什么意思。从中世纪幸存下来的手术工具极为罕见,尽管如此,手稿中的精美图画确有留存,这些图像至少能让人对中世纪的手术器械稍有了解。
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宰赫拉威(al-Zahrawi)的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他在其共30卷的著作《医学宝鉴》(Kitab at-Tasrif,英文译为The Method of Medicine)的最后一卷中对外科学作了讨论。它保存了大约200种手术器械的图示,这些形状狭长的器械图像夹杂在解释性文字的段落之间。
就像波斯医生曼苏尔(Mansur)的人体骨架插图一样——他将骨骼以示意图方式而非依照现实情况展示在书页上——这些器械的插图并不是为了向读者传达它们的精确形状和尺寸。无论是原始的阿拉伯语手稿、拉丁文译本,或是后来的印刷版本,宰赫拉威笔下的工具大部分都显得很薄,色彩斑斓,带有尺寸夸张的锯齿或者奇怪的、羽毛般的柔软感。
尽管如此,这些奢华的图片仍然清楚地表明这些物品对于撰写和整理这些书籍的外科医生来说有多么重要:他们花费了时间和精力来仔细传达它们手柄的华丽细节和末端精细的装饰,将它们作为昂贵、专业制作的物品呈现出来。
以这种方式展示器械也是在承认,他们的专业工具是外科公众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从事这项工作所需的合适设备意味着此人同时拥有能力和专业知识,就像如今,医生的手术设备或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诊断技术也许能让病人感到,他们正置身于一位训练有素且成功的专业人员的照料之下。
高质量的工具对于中世纪的外科医生重要至极,以至于我们经常在他们的遗嘱中发现它们被重点提及。中世纪晚期伦敦的一位外科医生安东尼·科皮奇(Antony Copage)的遗嘱终稿要求把他所有的钢制器械留给他的仆人乔治,条件是“他必须具有同样的技艺”。科皮奇的外科手术包与他的珍贵书籍、他最好的衣服,甚至还有一些留给他妻子的个人纪念品一起列在了遗嘱清单上,显然是他最宝贵的财产之一。
对手的描绘极其频繁地出现在医学、小说和诗歌等各类中世纪手稿的边缘空白处。
外科工具也令外科同业公会得以通过批准某些个人的行医资格来规范行业。这些公共机构可以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建立极高的名望。例如,在中世纪晚期的约克郡,理发师-外科医生同业公会是一股卓越的医疗力量,负责组织年度宗教剧目演出和授予新培训成员选举权等多种活动。
一些外行人士似乎偶尔会钻到空子: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的记录显示,一位名叫加洛普(Galop)的木匠被叫去给一位需要用锯子截肢的病人“进行外科手术”,这显然不是因为他有解剖学知识,而只是因为他拥有某种类似正确设备的东西。
尽管如此,对于被批准执业的专业人士来说,同业公会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工具,既赋予了他们专业身份,也赋予了他们社会地位。事实上,公会既能迅速给予执业批准,也能迅速收回它。如果发现成员违反规定——未能坚持缴纳会费,或是表现低于特定职业标准或道德标准——其人可能会被禁止行医,没收工具。剥夺他们的工具,就等同于剥夺他们赖以工作的双手。
中世纪的外科手术器械有时甚至被认为本身就具有某种内在的能动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触摸的能力标志着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区别,因此对完全信奉他的追随者而言,这种想法基本说不通:一把由冷硬的金属制成的手术刀或锯子不应该有任何生命力。但是,在中世纪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手中,这些沉重、一动不动的工具能够活过来。留存至今的外科器械的设计几乎总是有机的,并且极其生动。
器械的花纹近似叶状,配有闪闪发光的花瓣状镀金和嵌金银丝的蔓草纹镶嵌。还有一些工具上有着活泼的动物特征,如鹰头手柄或从设计主体中螺旋伸出的饰边象鼻图样,使它们的形状充满活力。人类的面部和嘴也很多见,它们出现在工具的手柄和衔接处。鉴于当时的医学论文通常修辞性地将外科手术称为一种“咬人的”手艺,这种以口固定的形象特别合适,因为作者会在文章中反复提及“咀嚼”、“大嚼”或“啃咬”的动作,既用来描述疾病的传播,也用于描述工具在病人体内的运动。
这些活泼的设计也与当时文学中对外科器械的描述相吻合,在文学这个虚构的领域里,外科器械甚至能更加生动地活转过来。在中古英语诗歌中,像锯子这样的工具——许多不同行业的人如屠夫、林务员以及外科医生都使用这种工具——不仅可以从它们刻有动物纹样的那一端观察四周,用它锯齿状的牙齿啃咬一切到嘴边的东西,还能说话。
一份来自莱斯特郡的15世纪手稿保存了一首名为《木匠工具之争》(The Debate of The Carpenter's Tools)的短诗。在这首诗中,木匠工作台上的一堆器具活了过来,在讨论要想让他们的主人富裕起来,怎样才是最好的办法,更紧迫的是,他们要如何加班加点工作才能供他这样毫无节制地喝酒。在斧子、曲柄锉和其他工具争论完后,锯子急切地加入其中,斥责前一位演讲者——指南针,为他醉醺醺的主人辩护:
你不过是在吹牛因为即使你昼夜不停地赶工,我得说他也不会成功。他和房东太太住得太近啦。
木匠的锯子,就像外科医生的锯子和刀一样,象征着辛勤的劳作和尽心尽力的技艺,体现了有生命的忠诚和匠人世界的常识。作为有知觉、能说话的存在,它们触摸病人的全身,变成了对它们亲眼目睹的外科世界滔滔不绝的评论员。比手稿的成书年代稍晚些,还有一把现存于维也纳的德国手术锯,在它的弓上刻有一首短诗。短诗在“spruch”这个德语单词上玩了双关,它既可以翻译成“锯子”,也可以翻译成“格言”,它提醒读者这些工具能够同时激发恐惧和希望:
我的躯体里投出残酷的目光,伴随着恐惧、软弱和巨大的痛苦,但当工作结束时,我的伤痛变成了欢乐。
***
对手的描绘极其频繁地出现在医学、小说和诗歌等各类中世纪手稿的边缘空白处。事实上,它们的出现频率比任何其他身体部位都高。这些图案现在被称为“手指符号”(manicule),图案中,纤细的手掌伸出极其纤长的手指,其中一根手指指向特定的一段文字。
这些小手是中世纪读者留下的遗迹,特意设计来让自己去注意一个重要的词组,一个特别重要的章节的开篇部分,甚至只是文本中的任意某处,由于如今已经难以忆起的原因,该书的主人希望在未来某刻重读此处。作为标记,它们通常附加在个人笔记前后,这些笔记也记在页边空白处,可能是由数个不同的人在手稿历史中的数个不同时刻写下的,这为书本的使用模式构筑了一种层次感。
这些页边的手只是中世纪阅读行为的数个诱人侧面之一,而这些侧面中有许多暗示着中世纪的阅读经历可能与如今的我们完全不同。根据描述,在中世纪,信件和其他通信来往经常由信使向在场的所有人大声朗读,而不是由收件人单独阅读。大多数日常阅读是在脑中默默进行,还是读出声来,这一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幸存的手指符号证实了在中世纪,阅读是一种多么强调触觉的操作。随着读者用手指划过一行行的文字,又用拇指推起页角来翻页,一些羊皮纸书籍因为反复经历这些动作而几乎变黑,以至于可以用现代文物修复员的机器(也就是密度计)来测量页面的相对不整洁程度,并分离出某个特定文本中最脏的部分——多半也就是最受欢迎的部分,书本的某一任主人也许曾一次又一次地翻阅这些段落。
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对读者提出警告,让他们不要如此粗鲁地对待这些昂贵的物品。10世纪的西班牙抄写员弗洛伦蒂乌斯·德瓦莱拉尼卡(Florentius de Valeranica)提醒读者,写作之痛苦与艰难:
如果你想知道写作的负担有多重:它使眼睛蒙上一层雾气,使脊背弯曲,折断腹部和肋骨,使肾脏充满疼痛,使身体饱经磨难。因此,读者呵,慢慢地翻页,让你的手指远离书页,因为,正如冰雹毁坏庄稼一般,草率的读者会毁掉书本和文字。正如港口令水手感到甜蜜那样,最后一行也令作者感到甜蜜。
然而,有些读者却情不自禁。阅读时的触摸不仅只是一种寻常的行为,令书页自然而然地累积起日常污垢:它也能标记出读者情绪激动的时刻。人们发现,罪人和恶魔的名字或配图上都有刮划、戳穿的痕迹,且污迹斑斑。另一些图片则因爱意被抹去,尤其是那些神圣人物的画像,常会被人们反复爱抚,乃至磨得一片空白。为了避免这种对神圣文本的意外亵渎,犹太人在阅读《摩西五经》时会使用一种名为“yad”(די,字面意思是“手”)的金属指示短棒,它的尖端通常真有一个微型手雕塑,以便隔着一段距离尊敬地追读经典。
除了磨损和弄脏手稿外,手指也是记忆手稿信息的有用工具。意大利音乐理论家阿雷佐的圭多(Guido of Arezzo, c.991—1033)用手概述了他学习歌曲的创新技巧。他编纂了一个六声音阶的音乐记谱法系统,这个系统历经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早期的积累发展而来,圭多给这个六声音阶系统中的每一个音符起了一个名字:ut,re,mi,fa,sol和la,它们在现代的唱名法中仍然存在。然后,他将这些音符一一置于手指19个关节点中的某一个上。
一份意大利语手稿中绘有描述圭多排列法的示意图,这份手稿现在仍保存在原处,位于意大利的蒙特卡西诺中世纪修道院(Montecassino),示意图显示,这些音符在手上展开,从拇指尖的G音符以螺旋路线移动,经过A和B两个音符到达手掌,随即经C、D、E、F四个音符横跨指根处,沿小指上升,重复G、A、B三个音,然后盘旋着跨过数根手指的指尖回到掌心。这样一个系统可以帮助个人按照各自的音阶记忆特定的复杂曲调,或许也让老师得以远远地朝学生比划音符,在他们排练新的赞美诗时以视觉方式来纠正他们的记谱。
如果说圭多式手法帮助歌手回忆起一段曲调或吟诵,或者帮助他们记下一段新旋律,以类似的形式,手也被用来直觉预感未来的事件。手相术——从某人的手中读出、预言未来事件的行为——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魔法实践,借由翻译详细的阿拉伯文资料,手相术被引入中世纪的西方,许多重要的医学文献也大致是从这条路线进入西方的。然而,医学研究倡导对宽泛的体液性质加以了解,并理解疾病在体内的传播,与之不同的是,手相家只关注细节,即手掌和手指不同部位的线条和斑纹的细微差别。
一份13世纪的英文手稿中画了一只魔法之手,上面写满了文字,帮助人们找到读手相的要点。手掌上的三条主线或掌纹在手的中心处形成了一个类似三角形的形状,从中可以读出生死的迹象,了解手的主人在战斗中表现是骁勇或懦弱,或者他们是死于水还是火。
几乎就在这种无声的修行成形之时,一种帮助僧侣们解决日常生活之必需的手势系统便迅速出现。
手指关节处堆肉表明这个人可能会有多个孩子,而且会轻易地避疾。手指的长度或指甲的曲度可能对其他一系列特征都有暗示,从腿部易受伤、智力水平高,到财源滚滚和性情凶残。
在这双手上,一整套精巧的微型符号系统盛行起来。指根处出现十字形意味着将有意想不到的厄运。一个像被划掉的字母“C”一样的符号预示着男子将升为主教,而一个形如“oo”的标志表明,手的主人或他的弟弟即将失去睾丸。当然,和今天一样,中世纪的人们对待这些所谓的预言的认真程度因人而异。
一些资料将这种行为简单地描述为愚蠢的游戏和误导性的巫术,但是在评估某人顾问的道德品行或者某人未来妻子的忠诚和贞操时,手相术观点通常会被包括在评估中,这说明手相学可能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严肃性(如果手相家确实态度严肃的话)。假如更仔细地观察一下,男人和女人会发现他们的胳膊末端携带着阅读、唱歌的工具,乃至他们一生的地图,而这张地图被分成小块刻在他们的身体上。
***
虽然圭多式的歌唱螺旋和手相示意图对我们来说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保存了中世纪的复杂思想体系,但是这些结构体系的存在本身是苦乐参半的。因为它们提醒着我们,在中世纪曾经存在过无数有关符号和象征的社会习俗,整套整套复杂的手势方言,而它们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
在这些已经佚失的手势系统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残留的文字描述窥得一斑。举例而言,影响力深远的诺森伯兰郡作家比德(Bede, c.673—735)在八世纪20年代写过一种复杂的手指计数法,这种方法通过让两只手以不同方式交叠、合拢和弯曲组合,可以比划出从0到9999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字。我们可以想象,在繁忙的市场上,手艺人或商人用这种方式比划价格,或是海员们在甲板两头朝彼此和海面互相比划。
而比德身为僧侣,能知道这样的习俗也并不足为奇。鉴于一些修道院对言论有严格的规定,手势系统对于像修道院这样的宗教机构的顺利运作是不可或缺的。克吕尼修道院(Abbey of Cluny)是法国东部一所颇具影响力的重要机构,后来亚历山大·杜索梅拉尔(Alexandre du Sommerard)的旅店正是以之命名,改成了克吕尼博物馆(Musée de Cluny)。
以10世纪克吕尼修道院里的僧侣为例,这些人特别重视宗教生活中的自我克制,倡导一种新的、集中的修道院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重视祈祷甚于其他许多常见的的人类行为。斋戒、禁欲、极长时间的歌唱祷告,还有祷告后严格维持的缄默是这一法国传统的特点。
不说话是为了避免造口业,也是为了通过模仿天使来让僧侣们的祈祷更好地传达(上界),因为克吕尼僧侣认为天使只会唱歌。然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烹饪、写作、耕地,这些都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机构的居民拒绝参与非天使性的对话行为而停止。
几乎就在这种无声的修行成形之时,一种帮助僧侣们解决日常生活之必需的手势系统便迅速出现。这种修道士用手指说话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很难推理复原,但在当时的数张手稿中保留了一份罕见的手势词汇表,它描述了大约118个指示地点、人物和事物的符号,这些符号是僧侣们需要知道的。在这其中,我们了解到:
要想比划出一盘蔬菜,就用一根手指从另一根手指上拖过,就像某人正在切要炒的蔬菜一样;要比划鱿鱼,就把五指张开,然后一起移动,因为乌贼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如果是针的标志,那就双手握拳撞击彼此,这标志着金属,然后假装你一只手拿着一根线,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针,而你想把线穿过针眼;要想用手势表达圣母,就用你的手指沿着前额从眉毛划到眉毛,这是女人的记号;为了表达一件好事,随便什么好事,把你的拇指放在你的下巴一侧,其他的手指放在另一侧,然后轻轻地(沿下颌线合拢)拽到下巴尖;如果想要表达一件坏事,五指摊开盖到脸上,假装那是一只抓住并正撕裂某物的鸟爪子。
我们发现的这种模糊的描述性证据越多,就越能看出打手势和手势本身是中世纪宗教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即使对那些不宣誓永远保持沉默的社群来说也是如此。那个时期的伊斯兰学者讨论了在传道时,神职人员的话语可以通过手的移动得到更清晰的表达,而在基督教弥撒期间,牧师被教导要高举并分开双臂,这个手势与基督在十字架上双臂张开的样子相呼应。在许多宗教场合,把双手合拢放在胸前同样是一种令人尊敬和强有力的举动,这一举动旨在与思绪和祈祷相伴随,鼓励信徒在撕开自身灵魂的同时将上帝拥在心口。
这些符号也会出现在大众宗教文化的物件中。触摸圣物盒能确保人们进入圣地,同时吸收因贴近圣遗物而带来的精神和身体的益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物盒也可以触摸回去。有些圣物盒的外形不仅仅是个精心装饰的盒子,而是完全成形的一双前臂,双手固定成祝福的手势。这不一定是由于圣物盒中装着圣骨(指骨、臂骨、肱骨或尺骨)。里面可以是任何圣遗物。实际上,受到珍视的恰恰是他们“做出手势”的可能性,这使得它们能够被拿到会众面前挥舞,仿佛它们真是圣徒本人的祝福之手,借此将圣物核心的神圣性传播到聚集的信徒之中。
在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手与健康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都得到普遍认可。
手势可以用大致相同的方式凝聚世俗社群。在法律界,举起双手或把双手放在圣经上作证,这与作证时给出的口头证词重要性相当,这点在当今的某些法庭上仍旧如此。婚姻契约也和一对夫妇的“绑手礼”密切相关,双方的手紧握在一起是订婚的象征。这种象征爱情的手势极受欢迎,以至于成对相握的两双手就像爱心一样,成为了恋爱象征物、纪念品和戒指上的流行符号。
一枚保存高度完好的14世纪胸针出土于柴郡的田野中。它由黄金制成,细腻精致,形状是两只带衣袖的手臂,两只手在胸针底部紧紧相握。这枚胸针背面的黄金没有经过任何装饰,以便展示其珍贵、闪亮的表面,但其他一些饰品有时也会刻有小花的细节——也许是令人心酸的勿忘我花,这种花对中世纪的恋人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甚至还有恋人之间的铭词,通常是英语化的法语:“想我”(pensez de moy)。
触碰在不那么浪漫的忠诚宣誓仪式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一个人可以通过念诵服从誓言来宣誓效忠于其国王或者哈里发,但是只有在双方握手过后,这一誓言才正式成立。这类手势似乎在许多皇家习俗中都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从早期的古典传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统治者要完成一系列繁复的仪式,其中包括被触碰和触碰他人。
在伊朗古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附近的纳克什·鲁斯塔姆墓地(Naqsh-e Rostam)里,一块3世纪的巨大浮雕刻画了萨珊王朝的国王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抓住琐罗亚斯德教神明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递给他的一个指环,指环象征着君权。在后来中东马穆鲁克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授衔仪式上,统治者要么手握、要么佩戴一把贝都因式的弯刀。欧洲的君主在加冕时,也会由大主教或其他高级神职人员在额头上涂上圣油,这让人想起《旧约》中先知撒母耳(Samuel)也是如此为备受尊敬的战士王大卫加冕。
到了中世纪晚期,君主本人的触摸,尤其是在这种加冕仪式之后,也已相应地转化成为一种非常珍贵的东西。这种触摸蒙受了许多神恩,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认为王的爱抚能够治愈各种疾病。淋巴结核(scrofula)是一种淋巴腺结核,它会导致颈部周围出现大面积疼痛和肿胀。这种疾病被认为非得用君主触碰治疗法治愈,以至于它得到了“morbus regius”这一拉丁名称,意为“帝王之症”,有时也被称为“国王之恶”。
从11世纪开始,法国和英国的淋巴结核病人获得特批与他们各自的君主会面,接受这种奇迹般的治疗。关于这种治疗手法的具体操作,记录很是模糊:一些皇室成员可能缓缓抚过患者的脸和脖子,而另一些可能只是拍一下他们的脑袋就凑合了事。不管是哪种,国王的双手都拥有清除重病的强大力量。
清洗这双皇家之手则更加复杂。在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手与健康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都得到普遍认可。古兰经的格言称,在祈祷之前应当净化身体,这演变成了定期的净身仪式,包括洗手、洗脚、洗脸,有时甚至是洗整个身体。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宗教礼仪,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洗手这一行为可能是真正的创造力驰骋之地。大约在1206年,阿拉伯学者、工程师加扎利(Ismail al-Jazari, 1136—1206)完成了他的《精巧机械装置知识书》(Book of Knowledge of Ingenious Mechanical Devices),在一系列可以追溯到9世纪巴格达的技术手册中,这是最为详尽的一本,其中概述了如何建造一系列机械自动装置,这些功能机器经常做成活动的野兽和人物的外形。
《知识书》的某些副本配有插图,伴随着加扎利细致的文字,彩色的示意图让这些作品变得生动起来,像一个个标签,和指导建造这些设计的详细笔记相对应。除了一个大象钟、一个可移动的四件式乐队、一扇能自动上锁的城门、一个机械化放血的模型以及许多其他物件,这些手稿中有一份对开本展示了一台机器,这台机器是加扎利受其赞助人、阿尔图格王朝国王萨利赫(Salih)委托建造的。
加扎利写道,国王“不喜欢女仆或女奴把水倒在手上为他净身”。为了帮他,发明家制作了一个巨大华盖形状的精巧装置。当国王拉动一根杠杆时,储存在其隐藏的上部水箱中的水的液压动力使装置顶部的一只鸟发出鸣叫。然后,水从一个由中空的铜制机械仆人支撑的罐子中稳稳地倒进脸盆里,仆人还拿着一面镜子和一把梳子,供他净身时使用。接着,另一只鸟把洗完的水喝干,最后,仆人自动垂下左手,做出一个收尾的手势,递给国王一条毛巾让他擦干。
把如此细致的注意力放在这双神圣的手上是有道理的。主持仪式的牧师张开双臂为教众祝福,外科医生则用手指状的工具在病人身上摸索,除去他们之外,在中世纪只有少数几个人的双手被赋予了令人敬畏的变换力,而国王正是其中之一。
中世纪的双手将世界纳入其中。它们的触碰塑造了经历、事物、人物和地点,从热蛤游戏里玩笑的打屁股到婚姻中的重要绑手礼,无所不包。在5世纪的著作中,圣奥古斯丁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双手依着自己的想法行动,他称之为“可见的文字”(verba visibilia)。虽然没有中世纪的手能够留存至今对我们“说”这种手势语言,但我们很幸运,它仍然在艺术品和习俗中残留有痕迹:签订合同、抓挠恶魔、教音乐,或下生死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自《中世纪的身体:中世纪的生与死》(Medieval Bodies: Life and Death in the Middle Ages)。杰克·哈特内尔(Jack Hartnell)是诺里奇东英吉利大学的艺术史讲师。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考陶尔德研究所(Courtauld Institute)、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任职。
文/Jack Hartnell
译/苦山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lithub.com/spanking-signing-reading-on-the-medieval-use-of-hand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来源: 利维坦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公众号
 科普中国微博
科普中国微博

 帮助
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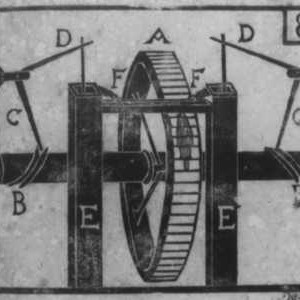 利维坦
利维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