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座山脉
不想与“山界之王”喜马拉雅比肩
但只有这座山脉做到了
它夹在喜马拉雅和昆仑两座超级山脉之间
仍诞生了世界第二高峰 乔戈里峰
以及一众超高山峰
(请横屏观看,飞机航拍视角下的喀喇昆仑山脉,乔戈里峰稳居C位,摄影师@王凯翔;标注@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又凭借海拔优势
积累超大规模的冰川群
坐拥世界级的超长冰川
在全球占据一席之地
(请横屏观看,喀喇昆仑地区冰川,摄于克勒青河谷附近,摄影师@毛江涛)
▼
它位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多国边疆
本应默默无闻,隐匿于众山之间
但这里总有诸多工程牵动人心
比如,上世纪60年代
中国联合巴基斯坦动员了上万人才建成的
中巴友谊公路
(请横屏观看,巴基斯坦的罕萨山谷中,中巴友谊公路,即“喀喇昆仑公路”,沿峭壁延伸,摄影师@王秉瑞)
▼
这里也总有事件吸引世人目光
就在2020年
中国在这条山脉东北部的加勒万河谷
击退了印度蠢蠢欲动的挑衅
捍卫领土完整
这座山脉就是
喀喇昆仑
(Karakoram Mountains)
(请横屏观看,喀喇昆仑山脉地形与位置示意,“喀喇昆仑”意为“黑色岩山”,制图@高俪倩&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它低调、冷峻、威严
却总在不经意间展露真正的实力
它为什么如此出人意料?
又为何拥有这般实力?
在星球研究所看来
它总是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以至于你可能没听过它的名字
但一定听过它的故事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去往中国的西部边境
从高度开始,去了解它奇迹的一生
01
最高耸的山脊
如果我们从新疆喀什出发
一路向南,穿过昆仑山
驶过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河谷
便来到了著名的红其拉甫国门
这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
唯一的陆地通商口岸
(红其拉甫国门,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摄影师@小强先森;标注@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在这里
你将与喀喇昆仑初次见面
即使是八月盛夏
周围山顶也有积雪残留
或许会让你忍不住“心动”
但醒醒
这不止是喀喇昆仑的美让你心动
还有此时的海拔已经上升至约4700米
稍微活动一下都能让大多数人
心率飙升、呼吸急促
发生“高原反应”
(红其拉甫国门附近雪山,摄影师@那阵风)
▼
不过想要见识真正的喀喇昆仑
眼前的海拔与美景显然只是开胃小菜
我们还需要更加深入
在中国边境
有一条山谷能让你看见真正的喀喇昆仑
那就是位于新疆叶尔羌河上游的支流河谷
克勒青河谷
河谷两侧
肉眼可见皆是高耸雪峰
(克勒青河谷与特拉木坎力冰川末端伸入河谷的冰舌,摄影师@王梓轩)
▼
其中南侧更加高耸
因为那里横亘着的是喀喇昆仑山脉的主脊
聚集着喀喇昆仑最高的山峰群
群峰之中
有身高8611米的世界第2高峰
乔戈里峰
(Qogir)
它一面朝向中国,一面朝向巴基斯坦
无论从哪个方向看
都呈完美的金字塔型山峰
它也是登山者口中的“K2”
垂直陡峭的巨型岩壁让许多人望而生畏
(不同方向的乔戈里峰,塔吉克语中有“高大雄伟”的意思,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王梓轩&毛江涛;标注@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还有身高8080米的世界第11高峰
加舒尔布鲁木Ⅰ峰
(Gasherbrum I)
(加舒尔布鲁木Ⅰ峰,摄影师@王梓轩)
▼
身高8051米的世界第12高峰
布洛阿特峰
(Broad Peak)
(布洛阿特峰,摄影师@王梓轩)
▼
以及身高8035米的世界第13高峰
加舒尔布鲁木Ⅱ峰
(Gasherbrum II)
(加舒尔布鲁木II峰,摄影师@王梓轩)
▼
山脊中央
四座8000米级山峰
彼此紧密排布在一起
犹如喀喇昆仑顶端最耀眼夺目的皇冠
而这也是世界上除喜马拉雅山脉之外
所有的8000米级山峰
(请横屏观看,克勒青河谷视角的四座8000米级高峰同框,摄影师@毛江涛;标注@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此外,群峰之中
还坐落着诸多7000米级、6000米级的山峰
譬如,众星捧月的玛夏布洛姆峰
(玛夏布洛姆峰,英文名“Masherbrum”,人称“K1”,海拔7821米,摄于巴基斯坦境内,摄影师@阿怪Zax)
▼
清冷凛冽的乌尔塔峰
(乌尔塔峰,英文名“Ultar-Sar”,海拔7388米,摄于巴基斯坦吉尔吉特,摄影师@王秉瑞)
▼
锋利无比的Laila峰
(Laila峰,6000米级山峰,摄于巴基斯坦境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如同利刃一般的Marble峰
(Marble峰,6000米级山峰,摄于巴基斯坦境内,摄影师@史飞)
▼
8000米级
7000米级
6000米级的众多超高山峰群
以极高的密度簇拥在一起
共同支撑起平均海拔超6500米的主脊
堪称世界上最高耸的山脊
相比之下
深切峡谷众多的喜马拉雅山
主脊的平均海拔也才约6000米
(请横屏观看,飞机上拍到的喀喇昆仑山脉,摄影师@张凌霄)
▼
主山脊之外
喀喇昆仑依旧不乏高山
不论你是从哪里看向它
迎接你的始终是巍峨雪峰
(请横屏观看,羌塘方向看喀喇昆仑东段边缘群山,摄影师@青木)
▼
如此海拔高度、如此密集的高峰
与地球之力的持续作用密不可分
特别是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之间
持续而剧烈的拼合、碰撞
这股力量创造了一列列超级山脉
也创造了改变亚洲的青藏高原
山脉中最知名的就是
世界最高山脉喜马拉雅山
而当我们看向喜马拉雅的两端
会发现多条山脉竟然扭曲在一起
如同打了个绳结
而喀喇昆仑就是西侧绳结中的一条
(请横屏观看,青藏高原地形与喀喇昆仑断裂带示意,制图@高俪倩/星球研究所)
▼
在此过程中
碰撞不仅使山脉隆起、扭曲
也让大地产生裂痕,形成断裂带
如果我们透过地表看向青藏高原
那里有无数条大大小小的断裂
其中有一条长约1200千米的断裂
斜穿了喀喇昆仑山脉
人称“喀喇昆仑断裂带”
断裂带两侧地块平移
形成所谓的走滑断层
进一步助力山地抬升
(走滑断层原理示意,制图@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就这样
大地错动又彼此挤压
再加上山体岩石质地坚硬
最终喀喇昆仑“高上加高”
成长为如今巨大、强壮、高耸的身形
可谓是最活跃的地壳运动
创造了最高耸的山脊
(请横屏观看,喀喇昆仑山脉主脊,山前是克勒青河谷的冰塔林,摄影师@陈德高)
▼
也使得喀喇昆仑
以喜马拉雅1/3的长度、1/3的面积
与其共同成为
世界上唯二拥有8000米级山峰的山脉
就连7000米级山峰的数量上
也仅次于喜马拉雅山
(请横屏观看,青藏高原7000米以上独立山峰归属示意,制图@高俪倩&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喀喇昆仑奇迹般的成为
青藏高原海拔最高的区域之一
如果我们乘坐飞机越过这片山区
看到的将是无穷无尽的雪峰
(请横屏观看,飞机视角下的喀喇昆仑山脉,摄影师@张凌霄;标注@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而当我们步入其中
又会被它迷人的身形击中心扉
那是一种极致高差所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
(请横屏观看,徒步者视角下的喀喇昆仑山,摄于巴基斯坦境内,摄影师@CDS在路上的二三事)
▼
为何单座山峰就会有如此高差?
这就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但实际上
这股力量早已遍布喀喇昆仑
无与伦比的海拔
建立了极为优越的低温储存环境
冰雪就此强势登场
一座堪称奇迹的“冷库”即将现身
02
最庞大的冷库
当我们继续从高处观察喀喇昆仑
最常见的除了雪山
就是山峰之间
冰雪长久累积而成的固态“河流”
冰川
这里的冰川不仅面积广阔
长度也独树一帜
(加舒尔布鲁木Ⅰ峰与巴尔托洛冰川,摄于巴基斯坦境内,摄影师@刘耕新)
▼
这里有世界第二长的高山冰川
锡亚琴冰川
(Siachen Glacier)
全长76千米
相当于1.5个港珠澳大桥的长度
或许你更熟悉它“世界最高战场”的称呼
锡亚琴在当地巴尔蒂语中意为
“野玫瑰生长的地方”
但由于印巴在这里的多次冲突
这朵“野玫瑰”却染上了些许血色
(请横屏观看,印巴边界的锡亚琴冰川,有时也翻译为“厦呈冰川”,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这里还有
67千米的比亚福冰川
(Biafo Glacier)
62千米的喜士帕尔冰川
(Hispar Glacier)
63千米的巴尔托洛冰川
(Baltoro Glacier)
59千米的巴托拉冰川
(Batura Glacier)
55千米的却哥隆玛冰川
(Chogo Lungma Glacier)
一个赛一个的长
(请横屏观看,巴尔托洛冰川,四周不断有支流冰川汇入冰川主干,摄于巴基斯坦境内,摄影师@邢嘉庆;标注@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像这样长度超过50km的山地冰川
在世界中低纬度范围内总共8条
喀喇昆仑独占其6
它们盘桓在喀喇昆仑最高的山峰群下
仿佛阻挡着一切外来的窥视
以至于想要靠近喀喇昆仑的超高山峰
我们往往需要在冰川上徒步数十公里
人行其中
只觉渺小如斯
(巴尔托洛冰川上的徒步者,远处的高山便是乔戈里峰,摄于巴基斯坦境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中国面积、长度均排名第一的山地冰川
同样在这片群山之中
那就是位于克勒青河谷附近的
音苏盖提冰川
(中国冰川排行榜示意,根据中国第二次冰川编目,普若岗日冰原没有计入其中,制图@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当我们从它的末端向上望去
42千米的长度
让人根本看不到尽头
只能看到冰川末端覆盖的大量碎石
(音苏盖提冰川,摄影师@张称心)
▼
然而
如果我们环顾喀喇昆仑四周
它的条件却看起来十分不妙
因为喀喇昆仑不仅深居内陆
周边还被一群超级山脉包围
因而整体降水较少,气候干旱
植被稀疏,山地裸露,荒漠成群
除了高度,似乎全无其他优势
(喀喇昆仑山南侧,巴基斯坦斯卡都附近的卡帕纳高寒沙漠,即“Katpana Desert”,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但它怎么可能只有高度这一张王牌
它要做的就是等风来
夏季
伴随着西南季风的风起云涌
来自印度洋的水汽北上南亚
尽管大部分水汽挥洒在喜马拉雅山前
仍有一小部分翻山越岭
抵达喀喇昆仑
到了冬季
西南季风退场
更高纬度的西风环流南移登场
将欧亚大陆西侧的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水汽
驱向青藏高原
拂过喀喇昆仑
如此便实现了一场“水汽大接力”
(喀喇昆仑山脉水汽来源示意,制图@高俪倩/星球研究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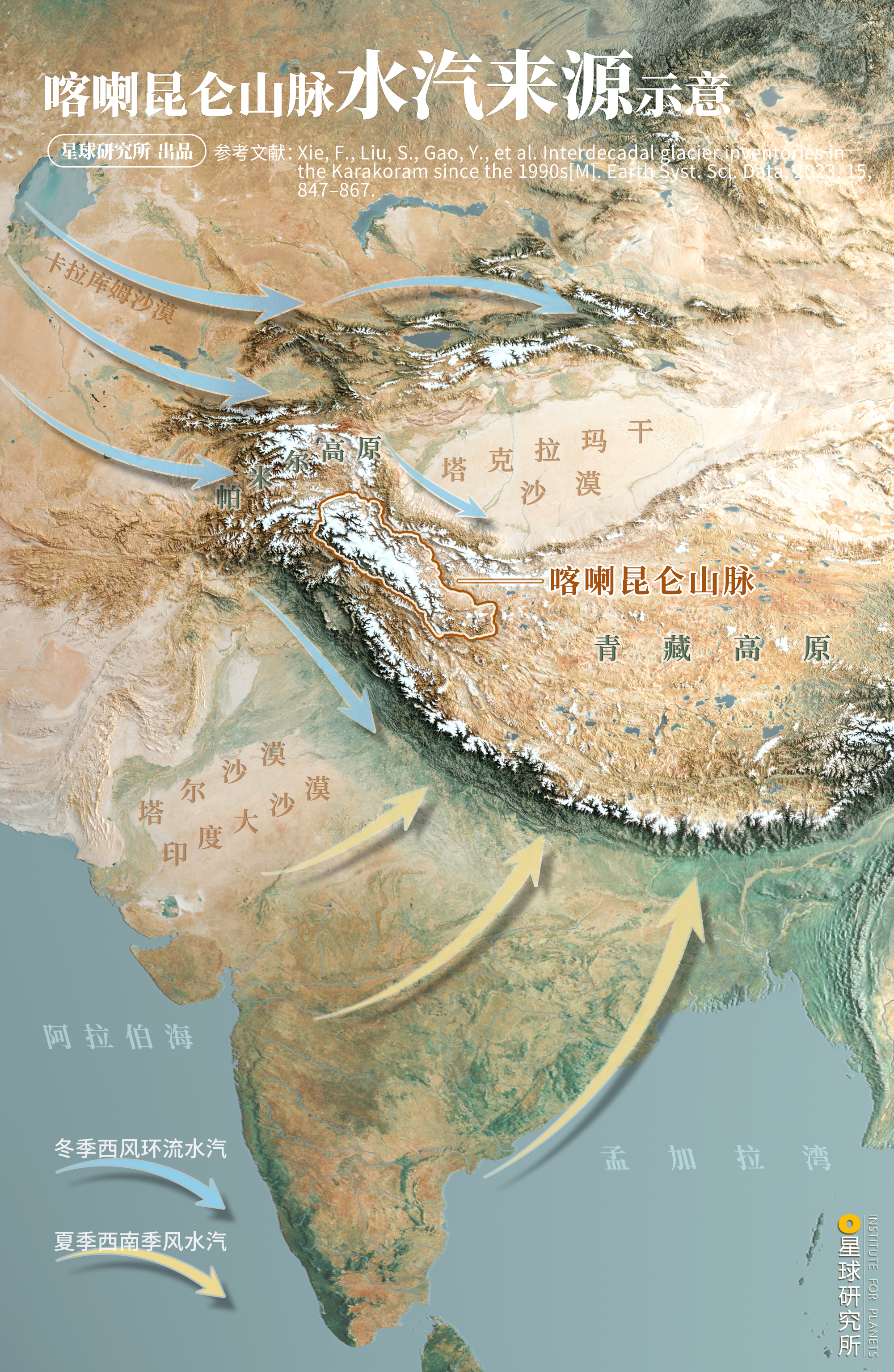
凭借超高海拔
喀喇昆仑截留了这些水汽
将其中的大部分化为高山的降雪
再者山脉本身纬度高、海拔高、温度低
能够更好的低温储雪
从而获得了充足的冰雪补给
累积出大规模冰川
(喀喇昆仑山的云海与雪山,摄影师@高立)
▼
如此一来
整个喀喇昆仑高海拔地带
就像一个巨型的天然“冷库”
长效制冷,循环制冰
奇迹般的孕育了1万多条冰川
覆盖了2万多平方千米的区域
即便放眼整个亚洲
它的冰川规模与喜马拉雅山
昆仑山、天山等超级山脉也几乎不相上下
是名副其实的冰川发育中心之一
(亚洲中低纬度冰川发育中心面积比较,制图@冰蘑菇&高俪倩/星球研究所;注意:冰川面积是动态变化的,不同年份的数值可能有所浮动)
▼
而相比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冰川
喀喇昆仑还有一个奇特之处
那就是它与众不同的发展趋势
工业革命以来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世界各地的冰川都面临着严峻的消融危机
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
在1990-2015年的25年间
就减少了约2553平方千米
相当于400个西湖的面积
(请滑动查看喜马拉雅山脉的多条冰川,在不同年份的对比图,图片来源@马春林&视觉中国)
▼
到了21世纪初,冰川学家惊喜地发现
喀喇昆仑山脉的大多冰川竟异常稳定
甚至隐隐有扩张的趋势
便将其称之为“喀喇昆仑异常”
超高海拔的保护
冬季降雪的增多
等诸多因素让“喀喇昆仑异常”
时至今日仍然发挥效用
(特拉木坎力冰川与银河,摄影师@赣州柒爷)
▼
于是
我们才能看到冰川
始终聚拢在山巅
(喀喇昆仑山的冰川,摄影师@王凯翔)
▼
悬挂在山坡
如同瀑布
(喀喇昆仑山的冰川,摄影师@阿怪Zax)
▼
还能继续雕刻各处山峰
(喀喇昆仑尖锐的山峰,摄于巴基斯坦境内徒步K2大本营的途中,摄影师@CDS在路上的二三事)
▼
挖掘山谷
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喀喇昆仑
(飞机视角下,喀喇昆仑山脉的巴托拉冰川、帕苏冰川,摄影师@张凌霄;标注@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你以为冰川就此完成使命了吗?
事实上它的影响极为深远
冰川不断凝结
同时也在不断融化
作为青藏高原最为庞大的冰川区之一
它承担着周边水源的关键补给
是周边生命的生息之源
(万米高空俯瞰喀喇昆仑地区冰川,摄影师@杜骏豪)
▼
03
最关键的补给
在喀喇昆仑严寒的高山上
只有最为坚韧的生命才能开出花来
(巴基斯坦境内,K2徒步路线上的翠雀花,摄影师@赣州柒爷)
▼
诸多生命向下寻求生机
但越向海拔低处,降水越少
幸好
河流出现了
它汇集着高处的冰川融水
在山脉内部横冲直撞
让山谷迸发生机
(巴基斯坦境内的罕萨河谷,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更重要的是
河流以高山冰川为源
穿过崎岖山地与干旱地带
为遥远的区域注入生息
如果我们从高空看向这里
就会发现
这样的河流不止一条
而是有无数条,分属三大水系
包括中国最大内流河 塔里木河
巴基斯坦最大河流 印度河
中亚最大内流河 阿姆河
它们以喀喇昆仑为顶点紧紧相拥
随后带着各自的使命奔向终点
(喀喇昆仑山脉周边主要水系示意,制图@高俪倩&松楠/星球研究所)
▼
作为三大水系交汇处的喀喇昆仑冰川
恰好有着最顶级的稳定
同时还有着最庞大的规模
能以最靠谱的实力
持续供应水源
(请横屏观看,巴基斯坦境内的吉尔吉特河,流淌在茫茫雪山之间,摄影师@;标注@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首先
在喀喇昆仑北侧
叶尔羌河自喀喇昆仑山主脊的多条冰川发源
加上昆仑山冰川的补给
叶尔羌河约70%的径流量来自冰川融水
(请横屏观看,喀喇昆仑山脉特拉木坎力冰川未端前的冰川堰塞湖,摄影师@郝沛)
▼
随着叶尔羌河向下游行进
它不断与塔什库尔干河等其他支流汇合
变得愈发壮大
(叶尔羌河、塔什库尔干河交汇处,摄影师@小强先森)
▼
甚至一举切穿昆仑山
冲出群山,奔向塔克拉玛干沙漠
成为塔里木河的上游主流
创造大片绿洲
(离开群山进入沙漠后的叶尔羌河,摄影师@陈剑峰)
▼
就在叶尔羌河的东侧
塔里木河水系的喀拉喀什河
也在奋力汲取冰川融水
跟随叶尔羌河的脚步
融入塔里木河水系
绿洲之中
诸多人类文明曾在此着陆
又跟着水源的拮据而没落
(和田县和皮山县交界的喀拉喀什河绿洲,喀拉喀什河别名“墨玉河”,摄影师@陈剑峰)
▼
与此同时
山脉南侧的印度河水系
也离不开喀喇昆仑冰川的供给
印度河虽发源于冈底斯山
但它上游的众多大型支流
什约克河、吉尔吉特河等
直接与喀喇昆仑地区的冰川相连
可以说印度河上游径流的1/3
来自喀喇昆仑冰川
奔涌的河流在喀喇昆仑劈出峡谷
其中落差最大的就有罕萨河谷
那里雪山环抱
周围耸立着一群7000米级高山
而谷底海拔只有2000-3000米
(请横屏观看,巴基斯坦的罕萨河谷,周围雪山林立,罕萨河是吉尔吉特河支流之一,摄影师@邢嘉庆;标注@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较低的海拔让它相对温暖
冰川融水又为它提供水源
重重山脉为它阻隔大多数的战事
这样的罕萨是巴基斯坦北部的净土
难怪《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
以罕萨为“香格里拉”的原型
每到秋季
罕萨都会染上一年之中最浓烈的色彩
山顶白雪皑皑
山坡层林尽染
谷底碧色河流荡漾
(请横屏观看,巴基斯坦境内,罕萨河谷卡利马巴德镇,摄影师@弥藏达娃)
▼
到这的旅人们
还会看到山谷高处
一座融入了西藏特色的古堡
它从罕萨王国时期就静立着
俯瞰这里的日月更迭、四季轮转
(罕萨古堡之一的Baltit古堡,融入了浓厚的西藏特色,站在古堡里可以俯瞰整个罕萨河谷,摄影师@邢嘉庆)
▼
离开喀喇昆仑后
印度河继续接收其他源于高山的支流
终于成为南亚的第一长河
诸多文明在此兴盛
除了塔里木河与印度河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中亚最大内流河 阿姆河
也从喀喇昆仑分得一部分水量
流经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四个中亚国家
是这些国家的母亲河
(请横屏观看,位于中国、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界的喷赤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此外,也有少数流水由于地形阻隔
在高原内部汇成了诸多湖泊
同样成为高原生命的宝藏
如,喀喇昆仑山脉最大的湖泊
班公湖
它的形状,细长如河道
2/3位于中国,1/3在印控克什米尔
作为内流湖的它
并非如很多人想象完全是咸水湖
它在中国的一侧
由于冰川融水补给丰富
反而成为了淡水湖
湖中鱼类成群,湖边水草丰茂
每到春夏之际
便会聚集成千上万的珍稀候鸟
(班公湖,位于广义上的喀喇昆仑山脉边缘,东接羌塘高原,南临喜马拉雅山脉,摄影师@章力凡)
▼
至此
哪怕深居内陆,哪怕没有主角光环
喀喇昆仑都在用实力
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这样一座山脉耸立多国边疆
注定会吸引勇敢的人前来
开辟另一番事迹
04
最勇敢的人群
如你所见
喀喇昆仑并不是一座容易亲近的山
高寒、缺氧
只是人们进入喀喇昆仑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雪崩、落石、泥石流、河水暴涨等
每一个都可能会让你落入生死险境
(雪崩,摄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喀喇昆仑山脉,摄影师@Xy E)
▼
即便困难重重、危机重重
千年前的法显、玄奘没有退缩
他们身负使命,怀揣勇气
先后从长安出发
穿越河西走廊,踏行过帕米尔高原
从不同方向踏上喀喇昆仑
传播佛教文化
(位于巴基斯坦吉尔吉特的Kargah摩崖佛像,摄影师@孙志军;标注@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往来中国西域与中亚、南亚的商旅没有退缩
他们走出的便捷通道
是庞大的“丝绸之路”网络中
极为重要的一环
(请横屏观看,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位于喀喇昆仑南麓,历来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站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临危受命的左宗棠没有退缩
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
他带领的军队曾直抵喀喇昆仑
建立当时海拔最高的驻兵点
赛图拉哨卡
(赛图拉哨卡遗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后来
常年驻守在神仙湾的中国官兵没有退缩
他们始终驻扎在这座
中国海拔最高的哨所之一
扼守着喀喇昆仑山口
(神仙湾哨所,摄影师@向文军)
▼
20世纪60年代
接到喀喇昆仑公路修建任务的兵团也没有退缩
这条路北起新疆喀什
南至巴基斯坦北部城市伊斯兰堡
全长1200多公里
中巴两国前后用了10余年时间
投入上万人,牺牲700多人
才修成通车
(巴基斯坦吉尔吉特的一处陵园,纪念因修建喀喇昆仑公路而牺牲的中国烈士,摄影师@王秉瑞)
▼
这条路穿过喀喇昆仑山等数条山脉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
也是世界上最难修建的公路之一
有人称之为“世界奇迹”
(喀喇昆仑公路示意,制图@高俪倩&冰蘑菇/星球研究所)
▼
其中的红其拉甫至吉尔吉特路段
纵穿了喀喇昆仑山脉
在高耸的雪山间穿梭
公路两侧落差极大
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是其中最核心,也最难修建的路段之一
(请横屏观看,巴基斯坦境内的喀喇昆仑公路,背后远处如无数宝塔垒砌的山名为“帕苏锥”,是喀喇昆仑公路的地标之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在工程施工之前
人们难以想象
一条人走马踏形成的小路能被修成宽敞大路
即便建成后
公路也屡遭自然的重创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10年
当时,巨型的山体滑坡侵袭了这条公路
大量落石堵塞在狭窄的山谷中
流水逐渐汇聚成一条狭长的堰塞湖
修好的公路从此被埋在水下
直到中国工程队另外打通隧道
才又得以通车
(现在的阿塔巴德湖,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现如今
大多数普通人已经不需要如此大的勇气
便可以欣赏喀喇昆仑
我们可以行驶在喀喇昆仑公路
仰望它的风采
也可以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
俯瞰它的风姿
但总有人想要更加深入
就有了
中国科考队在1987年
开启对喀喇昆仑的首次科学考察研究
就有了
无数探险者哪怕以生命为赌注
也要攀登以K2为首的一系列山峰
(此图摄于K2,即乔戈里峰,海拔8000米以上的瓶颈路段,登山者旁边就是30层楼高的冰瀑,经常会掉下巨大的冰块,让攀登者陷入险境,摄影师@高立)
▼
1954年,人类首次登顶K2
2004年,中国人首次登顶K2
2021年,人类第一次冬季登顶K2
至此世界14座8000米级山峰
全部完成冬季登顶
他们行走在冰川上
(喀喇昆仑山中的徒步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攀爬在冰岩混杂的峭壁间
化不可能为可能
(攀登者,摄于巴基斯坦境内,摄影师@高立)
▼
就这样
学者、商旅、军事家、筑路者、探险家
在喀喇昆仑来来往往
哪怕它冷酷、神秘、危险
可它也相当诱人、便捷
当我们真正了解过它
也忍不住被它吸引
此时的我们不再是旁观者
我们与它并肩看到了
世界第二高峰如何带领众山昂首向上
与喜马拉雅一较高下
(乔戈里峰日照金山,摄影师@Jerry)
▼
与它一起看水汽化为降雪
累积成山间的宽大冰河
绵延数十公里
(巴基斯坦境内的巴尔托洛冰川,摄影师@高立)
▼
与它俯瞰成千上万条流水
从高处向下流淌,汇聚成河
将所到之处的干旱变为勃勃生机
(透过飞机舷窗看巴基斯坦的罕萨河谷,摄影师@陈剑峰)
▼
与它看往来的人群
如何坚强地翻越山脉、开辟道路
打通往来交流的难关
(巴基斯坦境内,巴尔托洛冰川上的徒步者,摄影师@高承)
▼
同时也看到了喀喇昆仑
没有因身处超级山脉的夹缝而不再生长
没有因位于遥远边疆而远离历史轨迹
没有因无神话传说加身而脱离人类视野
最终凭实力走到众人面前
成为我们心向往之的奇迹
(请横屏观看,新疆阿克赛钦附近遥望喀喇昆仑山脉,摄影师@7556米)
▼
本文创作团队
撰文:王逻辑
图片:肩水都尉
设计:冰蘑菇
地图:高俪倩
审校:云舞空城&李楚阳&松楠
封面&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参考文献】
[1] 苏珍等. 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冰川与环境[M]. 科学出版社, 1998, 6.
[2] 张青松, 李炳元主编. 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晚新生代环境变化[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0.
[3] 张志军等编著. 喀喇昆仑南麓卫星遥感景观图册[M].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22, 1.
[4] 王英珊, 孙维君, 丁明虎, 等. 青藏高原冰川物质平衡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进展[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2025, 21 (2): 208-220.
[5] Hu Liu, Lei Wang, Jing Zhou, et al. Energy-balance modeling of heterogeneous glacio-hydrological regimes at upper Indus[J]. Journal of Hydrology: Regional Studies, 2023, 49.
[6] Xie F., Liu S., Gao Y., et al. Interdecadal glacier inventories in the Karakoram since the 1990s[J]. Earth Syst. Sci. Data, 2023, 15, 847–867.
[7] 刘方圆, 石正国. 全球变暖背景下中亚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及天山气候变化研究进展[J]. 地球环境学报, 2023, 14(1): 27– 37, 48.
[8] Li X., Long D., Scanlon B. R., et al. Climate change threatens terrestrial water storage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22.
[9] 朱颖彦, 潘军宇, 李朝月, 等. 中巴喀喇昆仑公路冰川泥石流[J]. 山地学报, 2022, 40(1): 71-83.
[10] 冀琴, 刘睿, 杨太保. 1990-2015年喜马拉雅山冰川变化的遥感监测[J]. 地理研究, 2020, 39(10).
[11] 董汉文, 许志琴, 曹汇, 等. 东喜马拉雅构造结东、西边界断裂对比及其构造演化过程[J]. 地球科学, 2018, 43(4):933-951.
[12] 陈亚宁, 李 稚, 方功焕, 等. 气候变化对中亚天山山区水资源影响研究[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3] 刘蛟, 刘铁, 黄粤, 等. 基于遥感数据的叶尔羌河流域水文过程模拟与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
[14] 许艾文, 杨太保, 王聪强, 等. 1978-2015年喀喇昆仑山克勒青河流域冰川变化的遥感监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15] 刘时银, 姚晓军, 郭万钦, 等. 基于第二次冰川编目的中国冰川现状[J]. 地理学报, 2015, 70(1).
[16] 朱颖彦, 杨志全, 廖丽萍, 等. 中巴喀喇昆仑公路冰川地貌地质灾害[J]. 灾害学, 2014, 29 (3) : 81-90.
[17] 李海兵, Valli Franck, Arnaud Nicolas, 等. 喀喇昆仑断裂带走滑过程中伴随的快速隆升作用: 热年代学证据[J]. 岩石学报, 2008, 24(07): 1552-66.
[18] Richard Phillips. Geological map of the Karakoram Fault zone, Eastern Karakoram, Ladakh, NW Himalaya[J]. Journal of Maps, 2008.